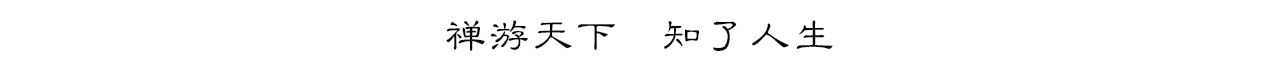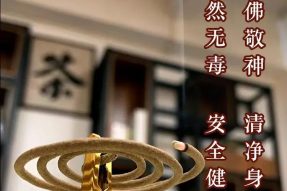解析唐代佛教寺院经济缘由
中古时期(3—9世纪)佛教的不断发展和寺院经济的日趋膨胀,对佛教寺院的组织管理尤其是经济管理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经历了南北朝时期寺院经济的发展和积淀,在唐代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寺院组织管理亦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佛教寺院经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制度变迁——《百丈清规》即创制于这一时期。对于《百丈清规》,学界多有论述,但主要集中于其农禅思想或佛教僧团的管理方面。本文则将《百丈清规》与唐代社会变迁和佛教发展尤其是寺院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予以考察,探究其在中古时代历史变迁下的影响和意义。
一、《百丈清规》的创制
长期以来,禅宗与律寺有着密切的关联,禅律共居。《景德传灯录》载:“以禅宗肇自少室,至曹溪已来,多居律寺。虽则别院,然于说法住持未合轨度故。”但随着禅宗的兴起和不断发展,其说法修行也不合当时之轨度。因此,对于禅门而言,需要制定相应的规制新例。唐代百丈怀海所立之清规,即是这一历史时期最为重要的创建。
百丈怀海,俗性王氏,福州长乐人。“少离朽宅,长游顿门,禀白天然,不由激劝。闻大寂始化南康,操心依附,虚往实归,果成宗匠。”他是马祖道一禅师的弟子。怀海“唯以道相授受,或岩居穴处,或寄律寺,未有住持之名。百丈以禅宗盛,上而君相王公,下而儒老百氏,皆向风问道,有徒实蕃”。可见,在禅宗日益纷扰的时代,百丈怀海还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对于清规的创制,《高僧传·怀海传》记载说:“后檀信请居新吴界,有山峻极,可千尺许,号百丈欤。海既居之。禅客无远不至,堂室隘矣。且曰:‘吾行大乘法,岂宜以诸部阿笈摩教为随行邪?’或曰:‘《瑜伽论》、《璎珞经》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随乎?’海曰:‘吾于大小乘中博约折中,设规务归于善焉。’乃创意不循律制,别立禅居。”宋代杨亿在《古清规序》中也说:“百丈大智禅师,以禅宗肇自少室至曹溪以来,多居律寺,虽列别院,然于说法住持,未合规度,故常尔介怀。乃曰:佛祖之道,欲诞布化元,冀来际不泯者,岂当与诸部阿笈摩教为随行耶?或曰:《瑜珈论》《瓔珞经》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随哉?师曰: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异大小乘,当博约折中,设于制范,务其宜也。于是创意,别立禅居。”
由此看出,百丈怀海主要是为了加强对禅宗丛林制度的管理和规范,对大小乘戒律“博约折中,设于制范”,才制定了“与律不同”的新的修行生活仪轨——《百丈清规》。而《百丈清规》所创这些管理制度和规范,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佛教自身特别是佛教生存与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说是中古时代佛教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制度变迁之一。
二、《百丈清规》与寺院经济的管理制度
在百丈怀海所创制之清规中,对于禅宗内部僧众行为有着制度性的规束。杨亿推原百丈立规之意就说:“或有假号窃形混于清众,别致喧挠之事,即当维那检举,抽下本位挂搭,摈令出院者,贵安清众也。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众烧衣钵道具,遣逐从偏门而出者,示耻辱也。详此一条,制有四益:一不污清众,生恭信故;二不毁僧形,循佛制故;三不扰公门,省狱讼故;四不泄于外,护宗纲故。”
也就是说,新的规制加强了禅宗内部的自我管理和约束,要求僧众抛弃以往“假号窃形、混于清众”的行为,而以全新的形象示于世人。为此,清规中制定了众多关于僧众日常生活和行为的规范律例。《大宋僧史略》中说:“后有百丈山禅师怀海,创意经纶,别立通堂,布长连床,励其坐禅。……可宗者谓之长老,随从者谓之侍者,主事者谓之寮司,共作者谓之普请。或有过者,主事示以柱杖,焚其衣钵,谓之诫罚。凡诸新例,厥号丛林。与律不同,自百丈之始也。”
同时,百丈清规还在寺院和僧众管理方面也进行了重要的创建,尤其在寺院经济管理方面,更是颇有新的创设。例如,在寺院经济的组织管理方面,百丈清规就设定了分工明确细致、僧众集体职掌负责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体制对后世影响深远,因而也得以流传沿革。从后世的清规中,我们大体可以了解《百丈清规》中关于组织管理的基本状貌。据《敕修百丈清规》的记载,寺院日常的生活管理是由东西两序负责的。其中关乎佛教寺院经济及僧众日常生活的管理者众多,兹举其重要者如下:
都监寺,古规惟设监院,后因寺广众多,添都寺以总庶务。“早暮勤事香火,应接官员施主,会计簿书,出纳钱谷,常令岁计有余,尊主爱众。”
监寺,也即寺主。总领院门诸事。
维那,“纲维众僧,曲尽调摄。堂僧挂搭,辨度牒真伪。……凡僧事内外无不掌之。”
知客,职典宾客。凡官员、檀越、尊宿、诸方名德之士相过者,负责接待,通报方丈。
副寺,古规之库头,今诸寺称柜头,北方称财帛,“盖副贰都监寺分劳也”。职掌“常住金谷钱帛米麦出入,随时上历收管支用”。
直岁,职掌一切作务。
此外,“列职杂务”中还包括化主、园主、磨主、庄主等各种杂务职责。
从以上所列管理职务来看,已涉及寺院僧尼生活的各个方面。其管理制度,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僧人各司其职,保证了寺院僧众经济生活的有序和稳定。《百丈清规》的这种管理制度,体现了农禅制度自我发展、自给自足的精神,提高了禅宗寺院经济的生存能力和发展空间,对后世寺院管理方式有着重大影响。
三、《百丈清规》对唐代寺院经济的影响
百丈怀海创制清规,不仅是为了禅宗自身的发展,而且是对佛教戒律的变通和适宜。将其置于中古时期的历史长河中,便可知《百丈清规》的产生是和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经济环境以及佛教的发展等因素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此处所要强调的是社会经济因素。唐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均田制废坏,土地买卖流转日渐频繁。随着私有制土地的发展,庶族地主势力的兴起,也使得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减弱。这种历史变化的潮流,对社会经济生活形成了严重的冲击。而寺院经济“双轨制”的发展,经济势力急剧膨胀,引起唐代朝野的极大关注,反对呼声不绝。安史之乱之后,社会环境剧变,佛教的生存发展空间受到严重影响,加之佛教尤其禅宗内部的危机,也要求佛教界对其自身的管理进行制度变革。面对如此困境,禅宗僧众创建了新的管理制度——《百丈清规》。《百丈清规》的这种管理制度,对于中古佛教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就《百丈清规》中的经济制度而言,对于佛教寺院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的制度即是百丈怀海所提出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普请法”。关于普请法,《敕修百丈清规》中称:“普请之法,盖上下均力也。凡安众处,有必合资众力而办者,库司先禀住持,次令行者传语首座维那,分付堂司行者报众挂普请牌。仍用小片纸书贴牌上云(某时某处)或闻木鱼或闻鼓声,各持绊膊搭左臂上。趋普请处宣力,除守寮直堂老病外,并宜齐赴。当思古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诫。”普请法要求僧众劳作时,除了“守寮直堂老病”外,一律参加。百丈本人也身体力行,作以表率。《祖堂集》记载说:“(怀海)师平生苦节高行,难以喻言。凡日给执劳,必先于众。主事不忍,密收作具,而请息焉。师云:吾无德,争合劳于人?师遍求作具,既不获而亦忘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言流播寰宇矣。”
“上下均力”的普请之法,确实在当时有着其独创的意味,它改变了以往寺院经济对于国家赏赐和社会捐助的依赖性,增强了自我生存发展的能力和独立性。吕潋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一书中指出,百丈行“普请”之法,“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上下共同劳动,耕种自给,这些规矩能达到整肃风气的目的。;任继愈则认为,禅宗保持了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他们的原则是自己劳动,自己消费,‘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从而在经济上立于不败之地”。
普请之法随着百丈怀海的倡导而渐趋广泛流播,同时也吸引了众多僧徒。例如普岸,因当时“怀海禅师居百丈山,毳纳之人骈肩累足,时号大丛林焉”,故而也来到百丈山,“日随普请施役,夜独执烛诵经,曾不惮劳,遂谐剃染”
普请法的推行,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变迁的趋势。随着唐代世族地主经济的渐趋衰落和庶族地主经济的日益兴起,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也得以继续发展。而佛教寺院经济在“双轨制”的发展膨胀下,逐渐遭到唐王朝的干预压制。安史之乱的打击和接踵而来的会昌法难,最终促使“普请法”的广泛推行。这为佛教寺院经济以崭新的模式发展开辟了道路。
其次,《百丈清规》推动了会昌法难之后寺院农禅经济的兴起。在安史之乱后,接踵而来的唐武宗“会昌法难”,是对佛教势力的又一次巨大打击。尤其是对寺院经济的摧残,可谓前所未有。尽管如史载那样,当时寺院废毁,还俗僧尼无数,但还是有相当多的僧尼逃逸四方,寻求躲避。如,衡山日照,“属会昌武宗毁教,照深入岩窟,饭栗饮流而廷喘息。大中宣宗重兴佛法,率徒六十许人还就昂头山旧基,结苫盖,构舍宇。复居一十五年”。五台山智頵,“及锺武宗澄汰,澦遁乎山谷,不舍文殊之化境。未逾岁载,宣宗即位,敕五台诸寺度僧五十人,宣供衣帔,山门再辟。願为十寺僧长兼山门都修造供养主”。
值得注意的是,在会昌法难之时,众多僧人得到佛教信众的保护和收留,并加以供养。如,大慈山寰中,“属武宗废教,中衣短褐,或请居戴氏别墅焉”;洛京广爱寺从谏,“属会昌四年诏废佛塔庙,令沙门复桑梓,亦例澄汰。乃乌帽麻衣,潜于皇甫氏之温泉别业。……大中初,宣皇诏兴释氏,谏还归洛邑旧居”。这说明在晚唐时期,佛教已在民间社会有着深厚的根底,受到各个阶层的信仰和认同。也就是说,在信仰层面上,民众并没有排斥佛教。而这也恰好说明,武宗废佛的矛头是直指佛教寺院经济。
尽管遭此劫难,但高僧大德们仍“罔亏僧行”,其宗教情怀并未改变。开元寺允文,“会昌三年,移居静林寺,专以涅槃宣导。属于武宗澄汰,例被搜扬,昼披缝掖之衣。夜着缦条之服,罔亏僧行,唯逭俗讥。大中伊始,复振空门,重整法仪”。正是这些僧众的坚守,为武宗之后佛教的恢复做好了准备。
当然,不可否认唐武宗废佛对佛教势力的沉重打击,但是,武宗废佛的经济劫难恰好给了禅宗一个发展的机会。因为法难的重点直指那些拥有大量田地、资财和劳动人口资源的寺院,而禅宗僧众却没有自己的独立寺院,寄居他宗寺庙。只有当百丈怀海于元和九年(814)创立了丛林规制,禅宗农禅制度才开始推行。其行普请之法,循“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规诫,自给自足,并不依靠国家外来支援。这也促使佛教寺院经济逐渐走向分散的小型化的发展道路。因此,禅宗在经济实力上而言,是无法和其他拥占大量土地、劳动人口以及巨额财富的宗派相比拟的。但正是如此,在会昌法难的浪潮中,其所受冲击和影响不大,更何况其农禅制度推行不久。故而,当会昌法难的风潮过后,在佛教的复兴过程中,禅宗能够成为佛教主流,且与王权社会保持了一种默契。可以说,禅宗在经济上推行农禅制度是这种“默契”形成的重要因素。
因此,可以说正是借助唐武宗废佛的转机,最终促成了《百丈清规》日后的流播盛行。唐武宗打击佛教寺院经济的行为,却促成了佛教禅宗和农禅经济的崛起:“(清规)其诸制度,与毗尼师一倍相翻,天下禅宗如风偃草。禅门独行,由海之始也”,这也可谓是历史的因缘会际。
四、《百丈清规》对唐后期佛教发展的历史意义
《百丈清规》的创制,不仅对寺院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于唐后期佛教自身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百丈清规》为唐代后期佛教的生存发展扩展了空间。唐代社会的繁华奢丽,在经历了渔阳鼙鼓下的喧嚣和尘埃之后,踏上了往昔不再的漫漫不归路。安史之乱是唐代历史的分水岭,也标志着中古时代的大变迁。当时北方社会遭到极大的破坏,“天宝末,贼将禄山掩有河洛,乾元之中思明继祸,中原鼎沸,涂炭生灵,十室九空,人烟断绝,少有疾疹,遂之膏盲”。在战乱动荡的年代,佛教也未能幸免,遭到了严重冲击。寺院废毁。僧众逃窜,寺院经济亦遭到相当破坏。西安碑林所存徐岱《唐故招圣寺大德慧坚禅师碑铭》记载说:“幽陵肇乱,伊川为戎,凭陵我王城,荡焚我佛刹。”李华《故中岳越禅师塔记》记载当时“狂虏逆天,两京沦翳,诸长老奉持心印,散在群方”。敦煌文书《讽谏今上破鲜于叔明、令狐嶇等请试僧尼及不许交易书》也载:“天下寺舍,翻作军营;所在伽蓝,例无僧饭。”
众多僧尼被迫逃往异地,寻求一方安宁。例如西明寺乘恩,避地姑藏,并在河西地区继续传布佛教。《宋高僧传》记载说:“及天宝末,关中版荡,因避地姑藏。……恩化其内众,勉其成功,深染华风,悉登义府。自是重撰百法论疏并钞,行于西土。其疏祖慈恩而宗潞府,大抵同而少闻异,终后弟子传布。迨咸通四年三月中,西凉僧法信精研此道,禀本道节度使张义潮表进恩之著述,敕令两街三学大德等详定,实堪行用,敕依,其僧赐紫衣,充本道大德焉。”《杜阳杂编》记载,开元中,巩县真如舍俗为尼,天宝末,由于“禄山作乱,中原鼎沸,衣冠南走”,真如不得不辗转流寓于楚州安宜县。
可以说,安史之乱,不仅仅形成对佛教思想的一种冲击,而且对佛教的生存空间也构成了威胁。这就使得佛教界不得不考虑在社会政治环境变幻下,如何保持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百丈清规》的诞生,即是这种社会背景下佛教自身制度变革的产物,它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
第二,《百丈清规》规整了佛教风气。在社会环境剧变所造成的外在压力存在的同时,禅宗自身内部也出现了危机。正如葛兆光所指出的:“过分的‘自然’给信仰者过多的‘自由’,过多的‘顿悟’使宗教修行无从立足,于是禅成了一种来自个人的感悟,瓦解了理性的约束,随心所欲的自然一旦冲破宗教的规范,自然适意可能变成自由放纵,从而导致‘狂禅’。”于是禅僧们行为约束放松,出现了放荡无拘的风气,坏佛像,烧木佛,食肉贪财,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云溪友议》记载:邓州有老僧,日食二鸱鸠,“僧俗共非之”,老僧终无所避;兴元县西墅有兰若,上座僧常饮酒食肉,群辈皆效焉。扬州孝感寺广陵大师,“形质寝陋,性多桀黠,真率之状,与屠沽辈相类,止沙门形异耳。好嗜酒贪肉……或狂悖性发,则屠犬彘,日聚恶少斗殴,或醉卧道旁,扬民以是恶之”。广陵的行为,不仅招致普通百姓的厌恶,就是僧众也对其有所不满。一老僧劝诫说:“汝胡不谨守戒法,奈何食酒肉,屠犬彘,强抄市人钱物,又与无赖子弟斗兢,不律仪甚,岂是僧人本事耶!一旦众所不容,执见官吏,按法治之,何处逃隐?且深累佛法。”但却遭到广陵的反唇相讥:“蝇蚋徒喋膻腥,尔安知鸿鹄之志乎?然则我道非尔所知也。且我清中混外者,岂同尔龌龊无大度乎?”耆僧的话,其实反映了佛教内部对于僧众种种放荡无束的行为会招致官方打击佛教的担心和忧虑。
禅宗宗教生活的自由放纵和信仰的无所依附,引起了佛教内部的激烈批评和反思。加之佛教在发展过程中,长久以来所形成的“弊俗”,更是招致了统治阶层的反感和厌恶。这些“弊俗”的蔓延,对佛教的发展空间更是产生了巨大的压迫感。
在禅宗思想上,以百丈怀海为代表的马祖弟子,主张“心如木石”式的清净境界,出现了向传统思想的回归转向。而南宗禅这种理路上的补救与逆挽,使百丈吓海一系僧人集团增强了凝聚力,最后成为南宗禅的主脉。而在这一过程中,《百丈清规》的创制即是改变这种局面的一个关键因素。《百丈清规》的成功,使得此后“他师所倡殊宗异者,虽各名其家,至于安处徒众,未有不取法子禅师者”。
《百丈清规》的创制和发展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当然与社会经济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有研究者认为,唐代均田制的实施,促使寺院经济高度发达,为中国化僧团制度的创建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实,唐代均田制实行僧尼授田的目的在于限制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但在实际绩效上,却成为寺院经济扩张的因素之一。而寺院经济的发达,也并不是为中国化僧团制度的创建打下物质基础;恰恰相反,唐代佛教寺院经济的膨胀,导致了后来直指其经济命脉的“会昌法难”。而禅宗农禅制度的建制和其经济生产的独立自主性,才使得其在武宗废佛风潮之后迅速发展。
上一篇: 襄樊佛教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下一篇: 宁波佛教旅游资源开发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