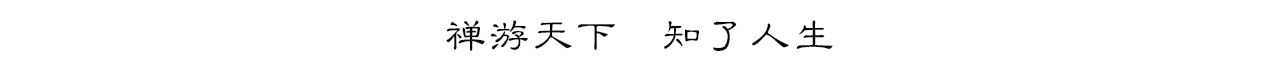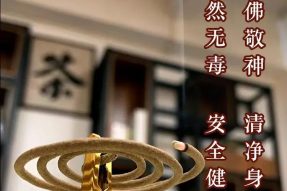相对于朝圣而言, 旅游可以说是一种更为大众化、世俗化的仪式。通过旅游, 旅游者从日常生活中的“原我”依次过渡到旅游过程中的“真我”以及旅游回归之后的“新我”。在阈限前阶段, 旅游者要交接日常生活与工作中的事务, 卸下往日的身份与角色, 收拾自己的心情与行装, 内心怀揣对理想境界的向往与追求, 开始从日常“原我”到非凡“真我”的过渡。在阈限期阶段, 旅游者完全进入一个与理想沟通与交融的神圣时空, 整个过程充满了真实神圣的氛围, 此时的旅游者追求心灵愉悦与精神自由, 其行为与以前呈现出明显的反差, 表现为一个自由、本真、纯粹的“真我”。在阈限后阶段, 旅游者结束旅游,“充电、再造”归来, 为往日“原我”注入了新的活力, 以“新我”的面目与原来的生活社会重新整合。
三、朝圣与旅游: 人类的精神文化“家园”
宗教是一种信仰, 更是一种文化现象, 旅游亦是如此。从外部意象看, 朝圣与旅游征途上的一切物化载体都是人类精神文化的显呈, 从内部结构看, 朝圣与旅游作为一种人生的“通过仪式”, 象征着人类的精神文化寻根。
(一)朝圣: 一种精神文化之旅
宗教作为一个庞大的文化象征体系, 囊括了众多诸如宗教物器、宗教制度、宗教行为等显形的与诸如宗教信仰、宗教教义等隐形的表现形态。朝圣作为一种典型的宗教行为, 集中展现了朝圣者内心的精神文化追求。
特纳在《基督教文化中的想象与朝圣: 人类学透视》一书中, 深入分析了早期欧洲宗教信徒们的朝圣缘由:“对于那些信仰基督教的奴隶和农奴而言, 法律本身就已规定它必须附属于特定的庄园或领地。他们的宗教生活也是受到地域限制的; 行政的教区也可以说是他们精神上的领地……于是, 朝圣者远离了每日居住和工作的地点, 前往一个神圣的遗址或是庄严的神坛去旅行、参拜……”[6]。我国学者陈国典关于藏传佛教朝圣者个案研究的田野记录中, 关于“藏族人为什么要朝圣?”问题的调研, 有的回答说:“朝圣是为了洗清自己的罪恶, 还能得到美好的来生, 特别是磕长头朝圣不仅能强身还能排解心中罪恶感对心身的压力。”有的回答说:“转经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想转就转, 或他人请我来代替他转。
转经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消除病灾、求得佛的保佑。”[7]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马贤在探讨千百年来穆斯林教徒不远万里、艰辛朝觐的真正目的和意义时曾写道:“……朝觐只为了完成自己所信仰的安拉对穆民规定的一项宗教义务,表示对安拉的虔信和敬畏, ……祈求安拉宽恕前愆, 使自己以‘重新出生’的清白身心, 走完未尽的人生之路, 以此来追求自己穆斯林属性的完善, 实现信仰和心理上的满足, 期望得到无比幸福的后世天国。”[8]
可以说, 朝圣路上的一切都被赋予了宗教的文化内涵,体现着精神文化的追求, 朝圣路上“居住中的行旅”与“行旅中的居住”的生命存在状态, 是圣徒们培养宗教情操的精进时刻。
自古至今, 千山万水挡不住朝圣者以身量地的脚步, 风霜雪雨浇不灭朝圣者一心向主的信念, 在历史的长河中, 一代又一代的朝圣者在为寻求自己精神家园的朝圣路上, 历经艰险, 近十余年来朝圣路上的有关伤亡数据也表明, 即便是在现代化的今天, 朝圣之路还依然充满了坎坷, 但人们朝圣的热情与决心却依然没有消减。朝圣是一种非常典型而又独特的宗教旅行活动, 朝圣者一路上的所见、所为、所悟无不深刻地表明, 朝圣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精神文化之旅; 同时, 朝圣作为一种三段式结构的“通过仪式”, 不仅是朝圣者在现实中完成身份转换的象征, 也是宗教信徒克制私欲、勤修苦行、净化灵魂、圆满今世、造福后世的阶梯。无论在外在形态还是在内在结构上, 朝圣都体现着“复命归真”的深层精神文化内涵[9]。
(二)旅游: 一种精神文化“朝圣”
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后工业现代社会里, 现代人更多地把追求目标转移到了心理、精神方面, 希望建立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 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渴望一种更轻松、更真实、更自然、更自我的生活, 后工业社会人们更是感到一种自身内部文化震荡与文化涵化的强烈需要, 而旅游便正好能使人的这种内心精神方面的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可以说, 现代旅游就是现代人为满足其精神心理需求, 而去各自的“圣地”探求自己的精神和文化价值的一种心灵休闲活动。物质日益富足、精神日显贫瘠的现代社会, 现代人渴望知识、友谊和理解, 追求自由、成就与幸福, 希望借助旅游来寻求不同的经历和体验, 从而不断丰富、改变、创造自己的精神素质, 实现自己的终极目标和精神价值。现代旅游者的这种多样化、多功能、高品位的精神文化需求, 直接导致了旅游动机和旅游本质内涵的精神文化性, 并寄寓和展现在旅游者整个旅途中的各项旅游活动之中。旅游与朝圣一样, 有着精神文化的动机与本质。
现代游客被旅游目的地“圣地中心”的独特文化所吸引,游客就像历代朝圣旅行中的“香客”, 旅游也就同朝圣一样,犹如人生的“通过仪式”, 成为一种类似宗教般的信仰笃信与行动虔诚, 为了抵达自己心目中理想的那一个个“圣地天堂”, 游客们背井离乡、潜心苦行地创造着一个个“天堂神话”。旅游与朝圣一样, 体现着精神文化的信仰与符号追求。在旅游阶段, 旅游者从日常的“自我中心”走向远处的“圣地中心”, 此时, 无所谓身份、职业与高低、贵贱之分, 在精神力量的驱使下, 所有人同吃、同住、同乐, 共同体验无拘无束地不带世俗“人格面具”交往的本真, 过着暂时返朴归真的生活。旅游与朝圣一样, 体现着众生平等的文化精神。旅游归来, 旅游者感到自己进行了一次内部的精神革命, 缓解和消除了自身的紧张与压抑, 经历和体验了异质的文化与生活, 寻找到自然真实的自我与人我关系, 感受到“天”、“地”、“人”的和谐, 精力充沛、焕然一新地回归生活。
旅游与朝圣一样, 有着精神的补偿与升华的功效。可见, 旅游是现代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种从“我者”走向“他者”, 从“世俗”走向“神圣”的神圣旅程, 集中体现着现代人的精神文化需求。由此, 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今涌现层出不穷的文化旅游热, 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文化背景越高的人往往其旅游动机也会越强烈。众多的事实表明, 在旅游过程中, 现代游客在追求旅游娱乐意义的同时, 更多地是追求旅游的精神文化内涵, 旅游是一种新形式的现代精神文化“朝圣”。
结语
20世纪末期, 朝圣和旅游被纳入了西方人类学考察的视野之中, 并且日渐成为人们关注的对
上一篇: 下一篇文章
下一篇: 武功山打造中华道佛养生旅游圣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