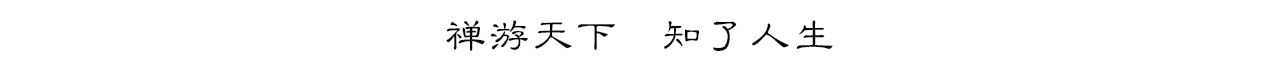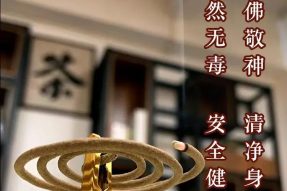当代汉传佛教寺院经济现状及其管理探析
作者简介:纪华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副主任;何方耀,华南农业大学宗教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汉传佛教寺院经济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传统的依赖地租及信徒布施等,转变为依靠门票、法事活动及寺院经营活动等新形式,寺院经济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为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从寺院管理模式看,目前汉传佛教寺院形成了7种不同的类型,因此在制定管理条例、实施管理规则时,应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管理制度,采用适合自身特点的管理模式。
[关键词]:汉传佛教;寺院经济;管理类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和实施,我国的佛教文化和寺院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汉传佛教寺院经济从空白到恢复,逐步走向繁荣,寺院数量已达3万多所,许多寺院已经基本具备适应现代社会的经济模式,为佛教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汉传佛教寺院亦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道场建设、组织制度建设、道风建设、佛学院教育、社会弘法和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服务经济社会建设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一、寺院经济模式的巨大的变化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过长时期与儒、道等中国固有文化的碰撞、融汇和相互吸收,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传佛教传统。古代的印度,寺院一般没有自己的生产和经营性活动,其生存运作基本依靠官府及信众的施舍捐赠。但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由于宗教传统、民族习惯及社会风俗的变化,寺院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禅宗丛林制度兴起之后,一改印度托钵乞食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农禅并重的新禅风。禅宗寺院外,一般寺院经济也由单纯的外来施舍捐赠,逐渐增加了寺院自身的生产和经营,形成了新的寺院经济模式。古代佛教寺院以地租为主,唐宋时期还形成了种植、浴室、碾硙、邸店、借贷等众多经营方式,因为寺院经营通常可以豁免赋税,有时寺院经济过于膨胀甚至会对国家经济产生影响而遭致打击,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灭佛”即有经济方面的原因。明清以后,寺院经济以施舍捐赠和地租为主,清末“庙产兴学”运动之前江南和岭南地区的佛教名刹往往拥有丰厚的庙产,如镇江定慧寺有土地万亩,金山寺有良田数千亩,常州天宁寺亦有寺田8500亩,广州的光孝寺、大佛寺、长寿寺都拥有走过5千余的肥田沃土。又如武汉归元禅寺创建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在清代200多年间,共有信徒布施白银2900余两、黄金10余两购置了19处地产,寺院自己则花费白银210两购置了3处田产,所以田租收入是该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除通都大邑的名山古刹之外,一般乡村寺庵则靠经忏佛事超度亡灵等以维持生计。但总体上,历史上的汉传佛教寺院均有恒产,有固定的经济来源,由于有着雄厚的寺院经济基础,汉传佛教寺院秉承大乘菩萨精神,积极实践慈悲利他精神,致力于赈灾济困,兴办各项慈善公益事业,为服务社会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体现了佛教寺院经济取之于社会并回馈于社会的传统。
清末“庙产兴学”运动给佛教寺庙经济以沉重打击,民国期间的动荡和战乱更使各地寺庙经济一蹶不振。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佛教生存与发展基础的寺院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51年土地改革运动,寺院田产按土改法重新分配,寺院经济由传统的以土地为基础的地租、庄园经济模式向现代经营行的转变,除部分山区寺院经营林场、果园(如苏州灵岩山寺)和农场(如江西云居山、广东云门寺)外,多数寺院兴办了毛巾厂、麻袋厂、服装加工厂以及火葬场等,基本实现了自养。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宗教工作座谈会,开启了党在宗教工作领域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1982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是党和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全面恢复的标志。1991年党中央提出了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至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进一步明确了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等内容。中共十七大、十八大都强调认真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促进宗教关系和谐协调,发挥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门票经济成为汉传佛教寺院重要的形式。汉传佛教寺院门票问题有其历史原因,“文革”期间,有些有历史影响的寺院由文物局或园林部门等管理,开始收取门票以供旅游参观。“文革”结束后,随着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这些寺院在恢复宗教活动场所后,为了实现“自养”,继续收取门票,其他一些寺院因处于旅游风景区等诸多原因也相继开始收门票。除门票收入外,信徒布施(寺院设功德箱、殿堂佛像修建化缘等)、宗教法事活动(以朝暮两堂功课随堂延生和超度佛事为主,也有大型的水陆法会等)、以及寺院经营活动等(包括素菜馆、佛经及法物流通处、卖香烛等)。
目前,我国寺院已有3万多所,在不同的寺院中经济情况大不相同。都市中寺院、佛教名刹与名胜道场以门票、寺院经营、佛事活动及信徒布施为主,经济情况比较好。然而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在寺院经济中也普遍存在。在一些大城市、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一些著名寺院的收入颇为可观,每年仅门票收入在2、3千万元以上的寺院比比皆是。在中国经济热点长三角、珠三角、江浙沪一带,甚至不乏年收入过亿的丛林大刹。以广东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初全省恢复4座寺院到2012年1500多座名刹古寺遍布南粤各地,其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不过,占绝大多数的乡村寺院,不少因地处偏僻,寺院无固定收入,信徒捐献有限,生存极为艰难,有的寺院常住还被纳入低保救济的范围。加之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差异性,造成一方面僧才难以为继,一方面僧人多向都市及名山名刹集中。大量乡村寺院和地处穷山僻壤的小庙不仅难见僧人,而且也难免处于“抛荒”状态。如湖北省佛教活动场所5000多处,佛教教职人员4000多人(认定备案近3000人),僧人多数集中在武汉、黄石等大中城市之中,或在宗教历史名胜区,如黄梅四祖寺、五祖寺等历史名刹,而多数乡村小庙甚至都没有僧人居住;重庆227处正式注册的宗教活动场所,200余处为偏远乡村的小寺院,多数都没有僧人居住,有的仅有一两位僧人;广东的湛江和潮州地区只有1、2个出家人的寺庙占当地寺庙的绝大多数,没有固定僧人,基本靠在家信众管理的寺庵也不在少数。
二、汉传佛教寺院所发挥的积极社会功能
改革开放30年来,汉传佛教寺院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回顾近现代佛教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可以说当代汉传佛教正处在黄金发展时期。目前中国佛教的社会形象基本上是好的,在社会上树立了正面的形象,随着佛教寺院经济的迅速发展,佛教四众在社会进步、文化活动和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总体上看,随着汉传佛教寺院经济的迅速发展,佛教界努力将取之于十方的善财回馈社会,积极从事于文化建设和弘法工作,努力投身于慈善公益事业,为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佛教寺院自古以来即具有双重属性,即宗教属性和社会属性,从佛教的传统理念来看,寺院财产取之于十方,亦用之于十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汉传佛教寺院秉承大乘佛教慈悲济世的精神,积极回馈社会。以慈善为例,据中国佛教协会不完全统计,仅2007年至2012年,全国佛教界就为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善款约18.6亿元,占全国宗教界捐款总额的62%。佛教公益慈善事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内容日益丰富、形式更加多样,透明度、公信力和号召力日渐增强,专业化、组织化、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佛教界已经成为全国公益慈善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汉传佛教寺院管理的类型
寺院经济的发展、寺院道风建设和寺院弘法利生事业都离不开寺院的有效管理,而经过“文革”浩劫之后,汉传佛教寺院的恢复和建设几乎都是在残垣断壁上重新起步,各地寺庙大都因陋就简、因地制宜,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恢复或重建寺院。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依靠各级党委统战部和政府宗教部门的帮助恢复和重建寺院;进入90年代中期,随着旅游业的兴起,除了政府相关部门之外,各种民间资本和地方势力开始涉足佛教寺庙的建设和开发利用;进行21世纪之后,“宗教搭台,经济唱戏”成为各地招商引资的流行模式,兴建寺庙成为各地开发旅游资源的重要措施之一,各种大型企业和商业集团以各种方式进入寺庙建设和管理,特别是那些风景名胜区的著名丛林,更是成为各种势力竞相投资的对象。因此,使佛教寺院的物业管理和经济管理呈现复杂多元的态势。依据目前的具体情况,就管理主体的角度而言,当下汉传佛教寺院的管理形式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七种类型。[2]
(一)僧人自主型管理。即寺院由出家僧众根据佛教的传统和仪轨,选任住持、礼聘两序大众,对佛教寺院的各项事务进行独立自主的管理,这既是我国相关宗教法规所规定的管理模式也是中国传统丛林制度一脉相承的管理体制。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无论是建立寺管会,还是实行方丈负责制,其管理主体都是出家僧众,除在对外宗教事务上接受宗教行政部门的领导外,其内部的大小事务,人事、财务、物业、法事、寺院建设、对外交流、自养事业都由住持率领下的两序大众决策、管理。就人、财、物、资源、信息管理的自主程度而言,那些完全依靠佛教界自己筹资兴建的寺庙最具典型性(如湖北五祖寺、四祖寺,广东六祖寺、千佛塔寺),就汉地寺庙的总体情况而言,其自主的程度和职事设置或许有所不同,但僧人自主型管理是大多数寺院所采取的管理模式。
(二)政府主导型管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一些寺院在恢复和重建过程中,政府职能部门扮演了主要角色,或者寺院完全由政府职能部门所建,或寺院作为旅游场所一直由政府相关部门管理。寺院恢复开放时,便是作为宗教场所和旅游景点双重身分登记注册的。虽然有僧人驻锡其中,按照宗教仪轨举行宗教活动,但寺院的寺管会基本由政府相关人员组成,并负责寺院或整个景区的管理和决策活动。这种管理类型的典型就是广东陆丰县碣石镇玄武山的元山寺。在这种管理体制之下,宗教场所和宗教活动被视为旅游场所或旅游景观的组成部分。[3]正如元山寺管委会汇报材料所说那样,“元山寺宗教文化是玄武山旅游景区最基本的文化载体,我们把玄武山定位为宗教旅游。海内外旅客到玄武山旅游、进香、朝拜是最基本的旅游活动,香火鼎盛,是海内外闽语系佛教信众信仰中心。”[4]“进香、朝拜”显然是宗教活动,却被视为“基本的旅游活动”。[5]将宗教活动和旅游活动视为一体,等量齐观,用管理旅游的方式来管理宗教活动,成为当地政府主导型管理的总体思路和指导思想。
(三)投资人主导型管理。即寺院由在家居士筹资兴建,本着谁投资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寺院建成后,法人代表和寺庵负责人都由投资者兼任,虽聘有出家人做挂名住持,但寺院中的出家人如同寺院所雇用的员工,只是负责法事活动,按月领取工资。筹资兴建寺院的法人代表既有商业人士,也有乡村的“大佬”甚至退休干部职工。这些寺院往往规模不大,以广东为例,主要分布在粤东粤西的乡镇,历史上它们就存在,但大多毁坏仅剩遗址,却被当地信众视为灵验之地,在落实宗教政策的过程,一些商界人士或当地“大佬”便筹资重建,作为投资营利的方式之一。如广东“普宁池尾的白水岩(寺),原为根通法师1949年前在此修行时所建,改革开放后申报开放,没有僧人,由那里的13个村轮流派大佬看班、收钱,聘请了一个僧人作挂名住持。还有揭东的源德禅寺,也属这一类型,名义上请光茂法师挂名住持,实为吴文蔡(已故)和他老婆管理、收钱。” 广东揭阳市东山区黄岐山凤内嘴口慈云禅寺也主要由在家居士管理,“香港的弘轮法师为挂名住持,实际操作的则为在家人,寺院里完全没有僧人。”[6]广东汕尾海丰莲花山的云莲寺也属于投资人主导型。[7]就广东的情况而言,这类寺院虽然数量不多,但在粤东的潮州、汕头、汕尾、揭阳等地却相当普遍。
(四)政僧合作型管理。即政府相关机关与僧人共同管理寺院相关事宜,一般来说此类寺院设有寺院管理委员会之类的管理机构,管委会由政府相关部门的人员和寺内常住共同组成,同时,寺内僧人也按传统清规设有方丈和两序执事,寺内的法务或佛事活动通常由僧人管理,而寺院的物业、旅游、附属商业网点和殿宇建设则由寺管会管理、决策,在寺管会内政府相关部门拥有较大的决策权。这种类型的管理以广东肇庆市的庆云寺较为典型。庆云寺寺管会由政府宗教部门的干部和寺内常住共同组成,寺管会的正副主任由市宗教局领导和庆云寺方丈担任,管委会下面采取企业管理中的经理制,每一个部门经理分管一个方面的工作,部门经理主要由在家人士担任。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管理体制,与寺院的恢复、重建的特殊经历有较大关系。庆云寺为广东省最早(1978年)恢复开放的寺院之一,在恢复之前寺院由云顶旅行社管理,庙里的僧人也如同职工一样由旅行社管理,整个寺院的重建、维修都是在政府的投资与主导下完成的,后来成立的寺管会也由政府相关部门起主导作用,1993年,一部分挂单僧人企图架空洪慈方丈,上访游行,寺内僧众内讧争斗,在政府宗教部门的强力干预下得以解决。这样在管理体制上这种政、僧合作式的管理模式便延续下来。
其实,各地寺院在开放初期,在寺庙的管理中或多或少会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影响,以广东为例,如韶关的南华寺、潮州的开元寺、广州的六榕寺都存在相同的情况,只不过在以后的调整中完成了体制转变,形成僧人自主管理的体制,而庆云寺、顺德的宝林寺等寺院则形成了政、僧合作的管理体制,并延续至今。[8]
(五)僧商合作型管理。即寺院由建设寺院的投资商和驻寺僧人共同管理,僧人负责寺院的教务活动,投资商则组成管委会负责寺院的财务、人事、物业和基建管理。这类寺院常常由从事商业的居士或信众团体筹资兴建,聘请出家僧人管理寺内的佛事活动。寺院的法人往往由在家居士(筹资兴建者)出任,管理寺院相关业务,聘请僧人为寺院住持,负责教务活动。这样便形成了商人(俗人)管理事务、僧人管理教务,僧商合作经营的管理体制。这类寺院就总体而言所占比例不大,就广东的情况而论,主要分布在粤东地区,如揭阳市的藏莲寺、侣云寺,潮州的松林古寺等寺院就属这种管理类型。
(六)家庭包办型管理。即俗人经营管理、以经忏法事为主要业务的“夫妻庙”或“父子庙”,主要为分布于福建、江西南部和广东梅州地区的香花庙,且为数不少。以广东的梅州为例,现在的梅州市除了千佛塔寺、佛光寺、石林寺、万福寺和丰顺、平远等县的一些寺庙外,绝大多数小庙都属于香花寺庙。[9]这类寺庙一般来说规模都比较小,由夫妻或父子管理,世代相传,其法事活动主要是给当地民众提供各种类型的宗教性服务,包括红白喜事上的念诵祷告、经忏法事,各种节庆上的祈福还愿、神祇祭拜活动。其活动虽然以佛教的面目出现,实为一种民间信仰。这类香花庙在广东梅州和福建地区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相传起源于明代),今天这类寺庙虽然逐渐减少,但在一些农村地区仍然广泛存在。[10]除了梅州地区之外,在粤东、粤西地区的乡镇也存在一些俗家人经营的“夫妻庙”。[11]
(七)政商僧三方合作管理型。即政府相关部门、大的商业公司和寺庙僧人三方或共同参与寺庙的建设和扩建,或将寺庙纳入名胜风景区并作为景区的核心部分进行管理,三方合作,共同经营管理,利润三方分成。如陕西的法门寺、海南的南山寺、佛教四大名山(峨嵋、五台、九华、普陀)的一些寺庙就选择了这种方式或者曾经是这种方式。这种模式是在世纪之交才兴起的,往往是由政府出面规划,商业公司出资经营,寺庙僧人则被迫卷入其中,这其中以重庆的温泉寺最为典型。这种模式虽然兴起不久,但由于受开发旅游、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驱动呈现迅速扩展的趋势,尽管国家宗教局等十部门于2012年正式出台法规,严禁寺庙“被承包、被上市”等现象[12],但这种三方合作经,以企业经营手法管理寺庙的模式仍然或明或暗地在各地悄然进行。
无论什么样的管理方式,关键看其是否符合管理对象的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事实上,这7种管理体制在不同的阶段都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即使如政府主导型和投资人主导型这样的管理模式,从佛教寺院的管理传统和政府宗教法规政策来看,它不太如法或合法,但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情况下曾发挥过良好的作用。如广东陆丰的玄武山元山寺,每逢农历正月初一到十五这两周之内,前来寺院烧香拜佛的海内外信众和游客多达十余万之众,长长的车龙从寺院一直延伸到高速公路,其场面之壮观、人员之庞杂在全省寺院中无出其右,在全国范围内也颇为罕见,如果不是政府的直接管理,仅靠寺内的十几位出家师傅,肯定是无法应付,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群体踩踏事件。[13]正是因为寺院由政府直接管理,政府相关部门可以从直接管理中获得较大的经济回报,因而也调动了其认真管理、全力以赴的积极性,以致元山寺开放30年来,基本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故,这与政府的直接管理不无因果关系。再如投资人主导型的管理模式,其寺院多在经济落后的贫穷山区,那里信众众多,但却没有正规寺院,一些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寺院则仅剩遗迹,而当地信众一时难以筹集足够资金重建寺院,一些从事企业经营的佛门居士发心筹集巨额资金,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庙宇重建,建好之后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主导寺院的管理,对寺院的重建和管理都起过积极作用。但对最近兴起的政、商、僧三界的联合开发模式,我们觉得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和警惕,因为这种由商业主导的捆绑式开发,对寺庙的建设和管理都具有极大的破坏性,造成的后果也特别严重,对这种模式和现象应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拟出有效的应对之策。
凡是存在的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这7种管理模式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先后出现,有其自身的因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过其正面作用,正因为这些不同的管理模式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曾发挥过积极作用,因此,在许多寺院得以延续至今,这种多元管理体制和不同管理模式事实上一直存在,尽管饱受批评和非议,却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这种作用是积极还是消极,与其时空环境有密切关系。
从辩证的角度来说,管理的多元性既说明了社会环境渐趋宽松,也说明了佛教寺庙管理上的多变与混乱。而这种多变与混乱在当下唯利是图的商业大潮的裹挟下,使寺庙管理出现了众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结语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佛教寺庙的发展也是如此,而就我国行政部门的传统而言,习惯于制定统一标准,实行统一管理,全国一盘棋,上下一个口径,简单明了,操作方便。但在当前情况下,身处不同环境中的寺庙却情形各异,问题迥别,在管理上形成7种模式,因此,在寺庙管理上也应因地制宜、区别对待,根据具体情况、因应具体问题,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管理规约,采用适合自身特点的管理模式。我们根据当下汉族地区寺庙的实际情况,对其管理体制进行类型划分、对其存在问题进行剖析就是希望既要看到各地寺庙的共性,更要了解其个性和特点;既要看佛教寺庙发展的良好态势,也要正视其存在的严重问题,在制定管理条例、实施管理规则时处理好统一标准和区别对待之间的矛盾和张力,让每一个管理规约都具有其明确的实施范围和适应对象,走出一纸规约通行天下的僵化模式,在统一管理与多元模式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使我们的管理思维跟上当代社会多元化的发展步伐,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应病与药。
注释:
[1]本文系国家宗教事务局2013年度“佛教寺院经济及管理模式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
[2]这七种管理模式的划分主要依据对广东佛教寺庙管理情况的调查和总结,参见何方耀《类型归纳、问题分析和对策前瞻——以广东佛教的管理现状为例》,载《广东民族宗教研究院院刊》2013年辑。
[3]1988年广东省宗教事务局的文件也指出:“陆丰县元山寺不在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行政领导下由僧人管理,而是由玄武山旅游区管委会管理,管委会及其党支部设在寺内,统管寺院的日常事务,僧人只被当作管委会雇用的职工。”参见广东省宗教事务局《我省当前佛、道教活动场所管理存在的问题》([88]粤宗发字53号),1988年5月31日印发。
[4]元山寺管委会《玄武山元山寺情况汇报》(未刊稿),2010年10月28日。
[5]《广东宗教事务条例》第五章规定:“本条例所称的宗教活动,是指信教公民按照宗教教义、教规及宗教传统、习惯进行的活动(广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2010年编印,第8页)。”因此,“宗教活动是指信教公民依照各自的宗教教义、教规和习惯进行的拜佛、诵经、受戒、祷告、礼拜、讲经、讲道、受洗、弥撒、终傅、追思和过宗教节日等行为。”见刘澎主编《国家·宗教·法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6页。
[6]资料来源于作者2009年6月30日在揭阳佛教协会的采访记录,采访人,何方耀;被采访人,揭阳市佛协秘书长陈君源。
[7]该寺始建于明末(1644年),初名云莲宫,清道光十年(1830年)重修扩建,易名云莲寺。1934年,毁于战火。1993年开始重建,主要由郑炎华居士筹资兴建(郑当时为海丰县政协委员,市佛协常务理事,副秘书长)。聘请新成法师为方丈,寺院由寺务委员会管理,主任为新成法师,副主任为郑炎华,实际为郑全权打理。资料来源:云莲寺采访记录,采访时间:2004年11月24日下午;采访地点:云莲寺客堂;采访人:何方耀、妙慧法师(时为《广东佛教》编辑);被采访人:郑炎华居士和寺院当家师。
[8]相关资料参见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关于我省几个主要佛教寺院的情况和管理体制问题的请示报告》(粤宗[(19)81]26号文);广东省宗教事务局《我省著名寺院、道观的基本情况报告》(粤宗字[(19)81]号文;广东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局《广东省的佛道教全国重点寺观移交和管理情况的报告》([85]粤宗发字136号文)。
[9]参见王馗《佛教香花——历史变迁中的宗教艺术与地方社会》,学林出版社,2009出版,第4页;李国泰《梅州客家“香花”研究》,花城出版社,2005年出版。
[10]关于香花佛寺的情况参见王馗:《佛教香花——历史变迁中的宗教艺术与地方社会》,书稿为作者对梅江地区14个香花庙进行实地调查的研究成果。14个庵庙包括田子庵、鸿盛宫、祥云庵、王明宫、遇灵庵、福云庵、白石庵、甘露亭、福缘庵、崇光寺、油岩寺(现已收归千佛塔寺管理)等寺庵。
[11]例如在1986年,宗教部门就发现雷州、海康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庵舍,完全由俗人管理,提供法事服务。参见广东省统战部《湛江市宗教工作调查情况》(省委统战部档案),1985年12月12日-22日。而笔者在2009年6月在揭阳调查时,也发现当地一个乡镇的一间观音堂为一女居士孙柔芳(70多岁)于十几年前申报,1995年开放后全权交由丈夫陈幕明管理,外人称为夫妻庙。僧人在其中挂单,专门负责佛事活动,收容一些游散僧人,最多时有僧人7-8人。
[12]参见国宗发[2012]41号文《关于处理涉及佛教寺庙、道教宫观管理有关问题的意见》,载《中国宗教》2012年第11期,第27-28页;另参见《南方都市报》2012年10月23日a20版的报道《十部门严管寺观“被承包”现象》。
[13]每年春节期间前来烧香礼佛的除了本地人外,还有众多的海外华侨华人,特别是东南亚的潮籍华人,人数达几万、十几万不等。游客人数最多的一天为正月初三,达数万人之多,为了应付这样的场面,寺院所在的碣石镇政府组成了200多人的寺管会,每年春节前汕尾市政府和碣石镇政府都要预先做出详尽的安全方案,动员全市的政府公安和交通干警,确保游客及寺院的秩序和安全。资料来源于采访记录,采访时间:2004年12月25日;采访地点:汕尾市碣石镇玄武山元山寺客堂;采访人:何方耀、妙慧法师(时为《广东佛教》杂志编辑);被采访人:元山寺当家师、碣石镇镇委副书记、陆丰县宗教科科长。另参见王杏元《碣石玄武山史话——神武今鉴》,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唐少凡、谢潮洲:《元山寺古今谈》,载卢木荣、陈波编著:《历史文化名城碣石》,2003年内部印刷本,第90-94页。
标签:蝉友圈 佛教朝圣 朝圣游学 佛教知识 佛旅研究 汉传佛教 寺院经济 寺院管理
蝉友圈www.livingc.com 印度朝圣 五台山朝圣 峨眉山朝圣 普陀山朝圣 九华山朝圣 终南山朝圣 鸡足山朝圣 南岳衡山朝圣 南华寺云门寺朝圣
上一篇: 朱维群:反对宗教极端主义要综合施策
下一篇: 论佛教文化的旅游开发—孙丰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