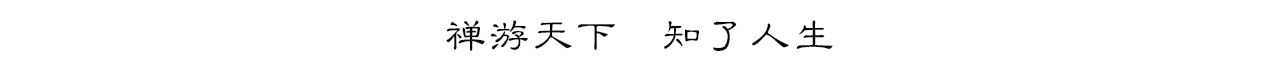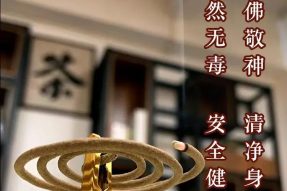王雷泉:中国佛教走出围墙困境及进入主流社会的路径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变迁过程中,主流佛教因义理不彰、组织涣散,无法满足民众爆发性的宗教需求。佛教因意识形态歧视和制度缺陷而形成的“围墙困境”,为权力寻租与资本逐利提供了巨大市场。政商利益集团利用佛教品牌特别是其中的神秘现象从事经济活动,侵吞佛教的发展空间。针对当前佛教的庸俗化与神秘化倾向,为彰显佛教智慧与慈悲的核心价值,本文进而分析“文化”的广、狭二种含义,确认宗教构成文化的终极价值和神圣意义。面对“法不归位”的现状,提出为信仰、政治、学术三极划界,分析佛教修行人、佛教社会人和佛教文化人各自的社会角色,应守住本份而互相提携。为改变佛教目前的边缘化状态,本文强调书院在佛教复兴和中国文化重建中的作用,培养造就能转变世道人心的佛教文化人,使佛教真正进入主流社会和精英人群,以提升社会对佛教智慧的认知,发挥佛教化世导俗的社会功能。
一、佛教复兴中的围墙困境
当前中国大陆佛教,正处在蓄势待发的复兴临界点。蓄势待发,指中国社会最近三十多年的急剧变革和日益融入世界文明体系,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变迁过程中,民众对佛教产生爆发性的宗教需求。尚处于复兴临界点,指社会对佛教的需求,与现存的体制性障碍形成巨大张力。这一围墙困境,导致正统佛教的供给严重不足,民众的信仰需求倾斜于外来宗教,甚至导致非制度化宗教的勃兴与外道邪教的泛滥。
当今世界70亿人口中,86%以上人口信仰宗教,但佛教仅占6%,远远低于基督宗教(33%)和伊斯兰教(22%)。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当今中国发展最快的不是佛教,而是基督新教。而佛教大量呈现为烧香拜佛现象,被宗教学界视为只是属于民俗信仰层次而已。在三大世界宗教中最先创立的佛教,为何在当今宗教版图中处于弱势地位?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佛教苦“墙”久矣!蒋孝严先生对大陆风景区的高额门票,特别是对寺院收费的质疑[1],可谓旁观者清。当今中国佛教被围墙困住手脚,面对基督教和港台佛教“兵临城下”的局面,为使佛教处于平等公正的发展格局,拆除有形和无形的围墙,正当其时。为回应蒋孝严先生的质疑,2010年8月,佛教界和文化学术界有关人士在东林寺举行关于“寺院与景点门票收费”的座谈会。笔者在会上指出:“给寺院设道墙收门票,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主要是在意识形态上依然有对佛教的歧视。我们要分清两堵墙:一堵是应该树立的,保护佛教纯洁性、神圣性的墙;一堵是应该突破限制弘扬佛法的墙,以利益大众和社会。”[2]
墙的第一重含义:维护佛教界合法权益。凝重肃穆的墙基,区分出神圣的世界与世俗的世界。佛教通过“结界”,以自然界的山林、流水之地形,或以僧团居住、修行、作法事等宗教活动,为自己划定特定的区域,以确保戒行无缺失,能够从事正常的修持活动。“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国王的士兵决不能进!”十八世纪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在波茨坦修建行宫,尚且不能侵犯农夫磨坊的产权,今天中国的寺院,岂能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3]
墙的第二重含义:隔断佛教弘传的体制性障碍。宗教的活力在于传播,佛教在世界宗教版图中的软肋是组织化和社会化程度,它必须真正建立在社会大众的基础上。把宗教活动场所限定在狭隘的寺庙围墙内,这在宗教管理制度的设计上,不能不说是一个败笔。中国佛教不具备如基督教那样与社区紧密结合的教会,更不要说基督教青年会那样的全国性组织。与基督宗教相比,佛教的手脚显然是被束缚住了。在独生子女的格局下,今后出家人会越来越少。如果佛教仅仅限制在寺庙范围内,在咄咄逼人的外来宗教强势包围下,佛教只能日益走向衰亡。
佛教的复兴是谁也不能抗拒的历史潮流,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这就隐含着极大的商机。如果说门票是佛教当初从废墟中复兴的不得已之举,那么现在已经演变为权力寻租与资本逐利的怪胎。政商利益集团利用有形的“墙”侵吞佛教的利益,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意识形态歧视和禁锢这道无形的“墙”。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经过政界、宗教界与学术界的拨乱反正,澄清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口号。到90年代初,以宗教可以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作为宗教政策的理论依据,以解决宗教存在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则提出要引导宗教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很多地方把神圣的、清静的宗教引向了商业化、庸俗化的邪路。
中国文化中的入世性和功利性,从古到今,从政府到民间,都要求佛教必须为现实服务,经忏佛事演变为商业性很强的“贩卖如来”,引起教内外诟病。天下名山僧居多,当佛教被局限于寺院范围时,“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短视政策及不当行为,使佛教受到的损害最为严重。一个世纪前“庙产兴学”的幽灵,现在依然在中国大地上徘徊,各种变种层出不穷,甚至演变成赤裸裸的“庙产兴商”,严重地损害佛教的声誉,透支佛教未来的发展空间。[4]
佛教出路在走入社会的广大人群,而不是圈在景区内,异化成佛教专卖店。当围墙成为某些利益集团攫取高额门票收入的工具,寺墙就成为隔断寺院与民众精神联系的障碍,抑制佛教事业发展的瓶颈。这种制度缺陷所形成的围墙困境,人为地在社会中制造了佛教信仰的供应短缺。权力与和资本勾搭,企图把寺院与风景区打包“上市”,侵吞的就是佛教品牌和无形资产,这是对佛教赤裸裸的掠夺。
政商利益集团控制佛教,把佛教作为政治或工商势力的附庸,甚至出于政治经济利益,把神圣的宗教变成迷信,是造成佛教庸俗化的社会原因。[5]在民众迫切需要宗教而佛教义理不彰、组织涣散的现时代,利用佛教特别是其中的神秘现象从事经济活动,简直是一本万利。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的《资本论》中,就已经借别人的话写道: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上个世纪80年代始,中国佛教在一片废墟中艰难地走上复兴之路。在佛教的主体性和宗教品格尚未确立之际,佛教或借助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或依傍政治威权,以打开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一状况,与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汉末魏晋时代非常相似。
《高僧传》的十科组织,继译经、义解之后,神异排列第三;而以儒家为本位的正史,为僧人入传的选拔标准,也主要视其与政治的关系及神通而定。但在佛教发展到盛唐时代,道宣的《续高僧传》则把佛教的核心价值戒定慧提升到前列,神异改为感通,降至第六位。[6]
太虚大师在《中国佛学》中,指出道安-慧远一系,乃为中国佛教的主动流。可以说,中国佛教的主流思想和组织建制,是循着佛图澄、道安、慧远师徒的事业而发展光大的。佛图澄藉助神通摄服残暴的统治者,为中国佛教教团取得了政治合法性基础;道安在战乱中,周旋于护持佛法的国主间,创制了僧尼规范,并推荐鸠摩罗什来中土译经;慧远身处佛法精神衰替的南方,以“影不出山,迹不入俗”的高行,维护了佛教的神圣精神。
慧皎在《高僧传·义解篇论》中,对道安、慧远二公的行事风格有如此论述:“涌泉犹注,寔赖伊人。远公既限以虎溪,安师乃更同辇舆,夫高尚之道如有惑焉!然而语默动静,所适唯时。”佛图澄之“神”、道安之“动”、慧远之“静”,表面看来相差极大,但精神实质则一,都是以真俗不二的智慧,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而采取的契时应机之举。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以道安、慧远的中道智慧与高僧风范,假如道安到了南方,也会有“影不出山,迹不入俗”之静;而慧远留在北方,照样会像乃师那样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之动。竹密不妨流水过,山高岂碍白云飞?道安-慧远一系,当涌泉犹注,冲决关山阻碍之后,毕竟东流入海,开演出中国佛教的主动流。[7]
二、中国文化的格局与士的使命
强调宗教要为经济建设服务,或者强调宗教是一种文化,都模糊了佛教的宗教色彩。佛教存在于世的根本是要化世导俗,不能光在外延为自己争取合法地位,要理直气壮地突出自己的宗教品格和主体性。这就需要对“文化”一词作一界定。
“文”,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后引申为语言文字、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及美、善、德行之义。“化”,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后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文化”,即“人文化成天下”,以与自然对举,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汉语中对“文化”的解释,表示文以载道、德以化人,本属精神领域,属于“小文化”范畴。
广义的“文化”,则将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全部内容,统统摄入“文化”的定义域。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称:“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所谓共业,就是社会群体所造就行为的共同结果,由此形成我们既定的文化和生活环境,包含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众多领域:认识的(语言、哲学、科学、教育);规范的(道德、法律、信仰);艺术的(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
器用的(生产工具、日用器皿以及制造它们的技术);社会的(制度、组织、风俗习惯)等等。
人处于天地和群己之间,不仅是社会的产物,更是人文化成的产物。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指出了人在社会关系和文化陶冶过程中,必须敬畏的三种力量。天命,是人文化成的终极价值源泉;大人,是领导世俗社会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者;圣人之言,是传承天道、教化社会的圣贤言教。在这三种敬畏对象中,天命和圣人之言,构成文化的终极价值和神圣意义。
士,作为天道的承担者、传播者、实践者、监督者,向上的路径是: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下达的路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即《中庸》所指出的文化路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由此可见,文化的价值源泉在天道,引领文化健康发展的主体是传承圣人之言的士,正如孟子所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儒道佛三教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主体。降至宋明以后,中国文化形成了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格局。
永明延寿:“儒道仙家,皆是菩萨,示助扬化,同赞佛乘。”(《万善同归集》)
孤山智圆:“修身以儒,治心以释”,儒佛言异而理贯,共为表里,可以互补。(《闲居编》卷十九《中庸子传》上)
憨山德清为学“三要”:“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而此三者之要在于一心。(《憨山老人梦游全集》卷三十九)
一切哲学,都是在求安身立命、安邦定国的道体,而其间的差异,不过是求道的深浅、广狭而已。民国建立之后,儒教随帝制覆灭而丧失了国教的地位。在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中,欧阳渐对儒佛的主次关系作了全新的阐述。在《孔佛概论之概论》中,欧阳渐认为就趋向人生究竟而论,孔学是菩萨分学,佛学则全部分学。根据真俗、体用不二的辩证关系,儒学若无超世出世之精神,则不能排除意、必、固、我之封执;佛学若无入世治世之方便,则流入顽空守寂的小乘境界。因此,佛不碍儒,得佛法而儒道愈精深;儒不碍佛,得儒术而佛法以普被。[8]
凡俗的生命之流生生不息,文化的血脉由上承天道、下化人生的圣贤而得以延续。佛教传入中国后,融入大乘菩萨的救世思想,“士”的弘毅精神和历史使命感进入更加超越的境界。这可以北宋张载的名言为标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融于历史,通于天地,方为大人。在中国走向强盛的现代化道路中,在对天理良心的呼唤中,佛教的作用日益凸现,已经成为朝野有识之士的共识。
三、佛教进入主流社会的路径
在物质主义盛行的当代中国,佛教思想有着巨大的对治作用。要真正落实人间佛教的宗旨,必须高扬佛教智慧和慈悲的核心价值,改变目前的边缘化状态,进入主流社会和精英人群中,以提升社会对佛教智慧的认知,发挥佛教思想化世导俗的社会功能。
中国佛教复兴过程中瓶颈现象的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是整个社会众缘和合的共业。所以我用“涉佛领域”这个词,表明这不仅仅是佛教界内部的问题,它已经进入公共领域。冲破当今中国佛教的围墙困境,改变佛教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共业,需要一切有志于中国进步的善男子善女人,以“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气概,为这个混浊世间注入一股股清流。
面对“法不归位”的现状,我们提出要为信仰、政治、学术三极划界,达到《大学》中“止于至善”的境界,即定位在各自的社会角色,守住本份而互相提携、互相制约,以达到和谐妥帖的境界。[9]
1、信仰核心:佛教修行人
佛教在社会中的地位,不仅仅是单纯强调佛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是强调佛教的主体意识,回到佛教了生脱死、弘法利生的宗教本位上。如果说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佛教界和学术界的这种观念,还是不常见诸公开报导的微弱诉求,那么在新世纪,强化佛教的宗教品格和宗教归属感,不仅是佛教界自身的要求,也成为政府宗教管理部门的施政理念。在信仰层圈,汉传佛教的一批少壮力量,借鉴藏传和南传的修学体系,正在探索佛学修学次第,重建制度和礼仪体系。由此从体达用,为人间佛教在社会的弘扬,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
2、社会层圈:佛教社会人
佛教存在于士农工商的社会生活中,与政治、经济各方面发生或顺或逆的关系。一方面,社会各界从事佛教事业和活动者,并非都是佛教徒;另一方面,佛教也必须走向社会发挥弘法利生的使命。那么,佛教的社会角色应如何定位?在组织制度上,明确佛教团体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定位,成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共识。社会对佛教的需求,使佛教的传播和教育,冲破了原来仅面向寺院场所和信徒的政策局限。面向社会各种形式的佛教教育蓬勃展开,改善和优化了佛教存在的社会环境。在信仰主体的重建和文化外延的扩展中,社会层圈中的政商力量,对佛教的正面支持也将日益增强。
3、文化外延:佛教文化人
从当前社会和文化各界对佛教的需求来看,人间佛教的弘化使命和目标,不仅仅局限在佛教修行人及佛教经营人,而是面对广大平信徒、佛学爱好者和非佛教信徒,培养造就能转变世道人心的“佛教文化人”。在文化层圈,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为佛教的思想所吸引和感召,在佛教文化的弘扬中,日益形成佛教教团的屏护,提升着佛教的文化品味,改善了佛教存在的环境。
从世界宗教生态环境的大格局下思考佛教的发展走向,为更多的朝野人士所接受。从目前“鬼打墙”的吊诡现状,改进为“佛跳墙”而海阔天空的格局。当今中国宗教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也催生着佛教酝酿新的弘传方式。借鉴基督教的传播方式,汲取台湾人间佛教运动的成功经验,已经成为佛教界内外有识之士的共识。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佛法是为众生而存在的,因此,“都市佛教”成为新世纪佛教的重要形式。在网络时代,山林与都市的界限正在消除。山林佛教的可贵,在于清净神圣的“山林气”,不是离群索居的逃世。都市佛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形式,但不能有陷入纷纭红尘的“市井气”。
《维摩经·方便品》描绘了维摩诘以佛教信仰为本位,在社会各界和文化领域的弘化活动:
“以资财无量,摄诸贫民。奉戒清净,摄诸毁禁。以忍调行,摄诸恚怒。以大精进,摄诸懈怠。一心禅寂,摄诸乱意。以决定慧,摄诸无智。”
“受诸异道,不毁正信。虽明世典,常乐佛法。”
“游诸四衢,饶益众生。入治政法,救护一切。入讲论处,导以大乘。入诸学堂,诱开童蒙。”
维摩诘在上述三大层圈中的互动,可归结为:“重建主体,改善环境;收缩核心,扩展外延。”收缩核心,即确立佛教的主体性和神圣性,并运用统一教会的权威促成四众弟子对高僧大德的向心力。扩展外延,即按照佛教事业的需要,从信仰层圈出发,向社会层圈和文化层圈拓展,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弘扬传播。
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主题:“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具有划时代的哲学革命的意义,恰能对治当前人欲横流、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病,也最具佛教进入主流社会传播的可操作性。并从三个维度阐释佛教改变世道人心的路径:
心净国土净:人与自然的关系。举凡资源、能源、环境等事关人类生存的紧迫问题,能够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
心安众生安: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于民生、社会稳定、政治体制改革、政教关系,教团体制及居士组织等课题,佛教理应像维摩居士当年“游诸四衢”、“入治政法”一样,起到化世导俗的职能。
心平天下平:人与世界的关系。评论和平与战争、宗教间对话、文明的冲突与和谐等课题。佛教界可以后来居上,提出自己独特的观点和立场。
四、书院在文化重建中的作用
“从因特网到因陀罗网,从知识经济到善知识经济。”这是对佛教在新世纪融入主流社会发展的概括。因特网的发展,不仅拓展了佛教传播的影响范围,亦改变着佛教自身的发展形态。知识与经济,这两种巨大的力量,只有在佛教精神的指引下,才能极大地推动人间净土的实现。
佛教是以改变人心而改变世道的。要让有力量者更有智慧,有智慧者更有力量。这就需要有更多的社会人群掌握佛教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宣扬真正如理的佛法,从而形成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
目前各类民间力量建立起来的各类书院讲学机制,成为当前佛教思想文化表达和传播的最佳平台。不仅推动刊物、教材和视听数据的发展,也蕴酿着具有现代管理模式的基金会一类学佛团体的出现,并为躁动于母腹之中、呼之欲出的佛教大学储备人才。佛教大学和书院的使命和目标,就是培养造就能转变世道人心的佛教文化人。[10]
1922年,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的演讲中,对文化作了如下定义:“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所谓共业,就是社会群体所造就行为的共同结果,由此形成我们既定的文化和生活环境。
太虚1929年在《文化人与阿赖耶识》演讲中认为,每个人的阿赖耶识与全人类所造之共业紧密相连,由此在时间和空间上延伸扩展,构成“文化的人”的历史和社会之两重意义。教育的意义,在于造就庄严完美的文化人,这些人必须具有在时间上继承以往文化,在空间上吸取异域文化,并创新发展,以至无尽未来的长处。
欧阳渐认为教育不应从民之欲望,趋时之潮流,应辨明教育的根本目的:
“教育不以兴国为的,而以民能充其所以为人之量为的。国可亡,天下不可亡,明不可失其所以为人耳。”[11]
要在一个义利不辨、师道不行的时代和社会,确立师道的价值。传授舍生取义之教,而非以“衣食住为业,发展维持强权为业,物质为业,人生日用支配为业。”
然而,现实却往往是使教育陷入名利场中,“师无其道,猴沐而冠,潮流所趋,又易以艺,梓匠轮舆,计功而食,贩夫鬻妇之场,叫嚣争斗不止,陵夷至于今日也!”[12]
从太虚和欧阳渐的论述可知:文化乃人类共造之业果,人不能离开既定的环境和条件而随心所欲。“共”的环境,体现为无数“不共”的个人行为。人类“恒”而“共”的社会历史,实由特立独行的“不共者”所引导而转动。故杰出人物所造的向善别业,可以推动改变众生的共业,从而推动时代的进步,改善社会的环境。
由此可见,书院这类文化教育机构,是佛教冲破当前“围墙困境”,进入主流社会和精英人群的平台。以舍生取义的豪杰之教为前提,培养立志办道的佛教文化人。(作者简介: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室主任、复旦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
(作者附识:本文据四次演讲(1、无锡灵山为复旦大学禅学会暨灵山公司中层以上干部,2011年7月9日;2、湖北黄梅四祖寺禅文化夏令营,2011年8月14日;3、北京龙泉寺,2011年12月17日;4、厦门闽南佛学院,2012年6月8日)的主要内容整合,于2012年12月7日提交上海玉佛寺“当代佛教与文化繁荣”学术研讨会。正式发表于《法音》2013年第1期。)
[1]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2010年7月11日在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称,大陆景点观光费用非常高。在他看来,寺庙等历史景点和黄山、张家界、九寨沟等自然景区,要么是老祖先留下的,要么是自然创造的景色,是中华儿女共同享有的,不应收取高额门票。在台湾,景区往往是低收费甚至不收费的。
[2]《关于“寺院与景点门票收费”的座谈会的纪要》,刊于东林寺《净土》,2010年第5期。
[3]王雷泉:《君子素其位而行》,《佛教观察》第八期卷首语(2010.01)。
[4]笔者曾撰文提出:土豪劣绅勾结伪劣僧对庙产巧取豪夺,将成为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它对佛教的破坏将是致命的。此处所谓“庙产”,是指广义的作为佛教教团这一主体所拥有的一切有形的物质财产和无形的知识产权。庙产掠夺者,盗用的是释迦牟尼的品牌,占领的是佛教未来的发展空间。(《世纪之交的忧思──“庙产兴学”百年祭》,《佛教文化》,1998年第1期)
[5]王雷泉:《佛教在新时代的社会化和组织化》,《法音》,2009年12期。
[6] 附表:
高僧传(14卷) 续高僧传(30卷) 宋高僧传(30卷)
(1)译经(35人) (1)译经(15人) 译经(32人,附见12人)
(2)义解(101人) (2)义解(161人) 义解(72人,附见22人)
(3)神异(20人) (3)习禅(98人) 习禅(103人,附见29人)
(4)习禅(21人) (4)明律(29人) 明律(58人,附见10人)
(5)明律(13人) (5)护法(18人)*增 护法(18人,附见1人)
(6)亡身(11人) (6)感通(118人)*神异 感通(89人,附见23人)
(7)诵经(21人) (7)遗身(12人) 遗身(22人,附见2人)
(8)兴福(14人) (8)读诵(14人) 读诵(42人,附见8人)
(9)经师(11人) (9)兴福(12人) 兴福(50人,附见6人)
(10)唱导(10人) (10)杂科(12人)*经师+唱导 杂科(45人,附见12人)
[7] 王雷泉:《涌泉犹注,寔赖伊人:道安之“动”与慧远之“静”——一个佛学研究者的手记之3》,佛教观察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25ebd50100gz10.html
[8]王雷泉编选:《悲愤而后有学—欧阳渐文选》,上海:远东出版公司,1996年初版,2011年修订再版。编选者序《悲愤而后有学》,刊于《佛教文化》1996年第2期。
[9]《君子素其位而行》,《佛教观察》第八期卷首语(2010.01)
[10]王雷泉:《佛教大学与佛教文化人》,《宗教问题探索》2007年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12。
[11]《致章行严书》,王雷泉编选:《悲愤而后有学—欧阳渐文选》,上海:远东出版公司,1996年初版,2011年修订再版。
[12] 《支那内学院院训释》,同上。
标签:蝉友圈 佛旅网 佛教朝圣 佛旅研究 中国佛教 主流社会 进入路径
佛旅网www.china84000.com 印度朝圣 西藏朝佛 五台山朝圣 普陀山朝圣 九华山朝圣 峨眉山朝圣 终南山朝圣 鸡足山朝圣 南华寺祈福
上一篇: 巫术与宗教对待失联客机的显著差异
下一篇: 孙永艳:太虚大师公民道德观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