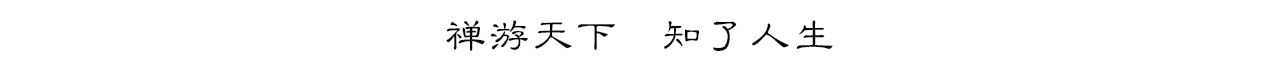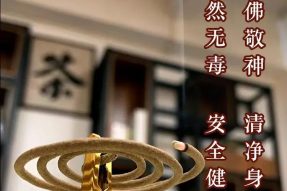禅宗六祖慧能
平民慧能
 六祖慧能,俗姓卢,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州),父亲名行瑫(tao),武德年间遭贬官,徙居到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贞观十二年(638)二月初八,慧能就出生在新州。慧能三岁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成人后,家境愈发贫寒,只能靠上山打柴和帮人做零活维持生计。
六祖慧能,俗姓卢,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州),父亲名行瑫(tao),武德年间遭贬官,徙居到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贞观十二年(638)二月初八,慧能就出生在新州。慧能三岁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成人后,家境愈发贫寒,只能靠上山打柴和帮人做零活维持生计。
有一天,慧能上街卖柴,有位顾客买了他的柴,令他把柴送到旋店。在旋店的门口,有位客人在诵经,慧能听了,似有所悟,久久不肯离去。他上前向客人打听读诵的是什么经。从客人的介绍中,他得知五祖弘忍禅师在蕲州黄梅冯茂山传法,并经常劝告道俗信众读诵《金刚经》。慧能听了,心中遂产生北上求法的念头。但因为母亲尚在,不能立即前往。
北上求法
慧能三十三岁的时候,母亲去世。安葬了母亲之后,慧能便取道韶州曹溪(今韶关)北上求法(此说与《六祖坛经》所记不同)。在韶州,他结识了德行之士刘志略,因为情投意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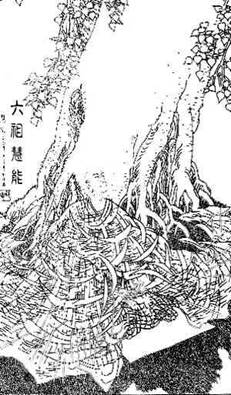 结拜为兄弟。刘志略有个姑姑,是位比丘尼,名无尽藏,住在当地的山涧寺,经常读诵《涅槃经》。慧能白天与刘志略一起参加劳动,晚上则听无尽藏比丘尼读诵《涅槃经》。慧能虽然不识字,但他的悟性极好,经常在听完经之后,给无尽藏比丘尼解说经文的大义。有一次无尽藏比丘尼手捧经卷,向慧能请教一个字的读法和意义。慧能回答说:“字即不识,义即请问。”无尽藏比丘尼说道:“字尚不识,曷能会义?”慧能回答道:“诸佛妙理,非关文字。”无尽藏比丘尼听了,非常惊异,知道慧能是个有道之人,心生敬意。这样一来,慧能的名声很快传遍乡里。虽然当时慧能还没有出家,但是当地的信众都争相前来瞻礼和供养。并且在附近的宝林古寺旧址上,为慧能建了一座道场。慧能在这个地方一住就是三年。
结拜为兄弟。刘志略有个姑姑,是位比丘尼,名无尽藏,住在当地的山涧寺,经常读诵《涅槃经》。慧能白天与刘志略一起参加劳动,晚上则听无尽藏比丘尼读诵《涅槃经》。慧能虽然不识字,但他的悟性极好,经常在听完经之后,给无尽藏比丘尼解说经文的大义。有一次无尽藏比丘尼手捧经卷,向慧能请教一个字的读法和意义。慧能回答说:“字即不识,义即请问。”无尽藏比丘尼说道:“字尚不识,曷能会义?”慧能回答道:“诸佛妙理,非关文字。”无尽藏比丘尼听了,非常惊异,知道慧能是个有道之人,心生敬意。这样一来,慧能的名声很快传遍乡里。虽然当时慧能还没有出家,但是当地的信众都争相前来瞻礼和供养。并且在附近的宝林古寺旧址上,为慧能建了一座道场。慧能在这个地方一住就是三年。
有一天,慧能突然想起求法的事来,私知念言:“我求大法,岂可中道而止?!”于是第二天便离开了宝林寺,继续向北行进。经过乐昌县西山石室间的时候,慧能遇见了智远禅师,并向智远禅师请教有关坐禅的一些事情。智远禅师告诉他说“观子神姿爽拔,殆非常入。吾闻西域菩提达磨传心印于黄梅,汝当往彼参决(我看你神姿清朗超拔,恐怕不是一般的人。我听说菩提达磨从西域来到中土,传佛心印,展转至于黄梅五祖,你不要再耽误时间了,速往忍和尚处参学,以决生死之疑)。”
与五祖对偈
于是慧能一路风尘仆仆,直造黄梅五祖道场。
慧能自幼生活在岭南,目不识丁,生得瘦小,一幅山野樵夫的模样。所以五祖初见他的时候,便戏称他为“獦獠(ge lao)”。《五灯会元》、《祖堂集》和《坛经》等书,都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这次见面的情景–
五祖问:“你从哪儿来?”
慧能道:“从岭南来。”
五祖问:“你到这里想干什么?”
慧能道:“不求别事,只求作佛。”
五祖道:“你这个獦獠,又是岭南人,你怎么能够成佛呢?”
慧能道:“人虽然有南北之分,佛性却没有南北之别。我这个獦獠,形象上虽然与和尚不同,但佛性又有什么差别?”
五祖听了,知道慧能根机很好,不是常人,本想继续跟他多交谈几句,但因为徒众都在左右,担心慧能日后会遭到众人的嫉妒和排斥,于是便把他打发到碓坊舂米。舂米是一件苦差事。慧能生得矮小,体重不够,为了踏碓,他不得不在腰间拴上一块石头。就这样,慧能昼夜不停,勤勤恳恳地舂了八个月的米。
衣钵之争
有一天,五祖把大众召集到一起,告诉大众说:“生死事大,无常迅速。我已经老了,当选一名接法人,以确保祖师的法脉不断。佛法不可思议,贵在实证,你们万千不要以为记住了我所说的法语,就算了事。你们且下去,各自根据自己的修行体会写一首偈子给我看看,如果有人契悟了佛意,我就把法衣传付给他,立他为六祖。”
当时,五祖会下,有七百多名僧人。其中,以神秀上座最为出色。秀上座是教授师,兼通内外之学,经常为大众讲经说法,并且得到了五祖的器重和众人的敬仰。因此,大众退下来之后,共相议论道:“六祖之称号,除了秀上座之外还有谁能够担当得起呢?我们不用劳心费力写什么偈子了,等秀上座得了法衣成为六祖,我们都依止他就完事了。”
 听到大众的议论,神秀想,大众之所以不敢写偈子,是因为我是他的们的教授师。我应该向大和尚呈上偈子。当然,我呈偈子是为了求法,而不是为了夺取祖位。如果我不向大和尚呈偈子,大和尚怎么知道我心中见解的深浅呢?我又如何能得到五祖的传法呢?翻来覆去,左思右想,折腾了两三天,神秀终天作出了一首偈子,并趁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写在廊壁上,偈曰:
听到大众的议论,神秀想,大众之所以不敢写偈子,是因为我是他的们的教授师。我应该向大和尚呈上偈子。当然,我呈偈子是为了求法,而不是为了夺取祖位。如果我不向大和尚呈偈子,大和尚怎么知道我心中见解的深浅呢?我又如何能得到五祖的传法呢?翻来覆去,左思右想,折腾了两三天,神秀终天作出了一首偈子,并趁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写在廊壁上,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第二天早晨,五祖经过的时候,忽然看见此偈,知道是神秀所作。这首偈子虽然没有明心见性,但是,后人如果依此偈修行,还是可以得天大利益、免堕恶道的。因此,五祖还是当着众人的面对这首偈子大加赞叹,并且要求大众焚香读诵此偈,依偈而修。但是,私下里,五祖还是告诉神秀说:“你的这首偈子,还没有明心见性,见地还不到位,还在门外。如此见解,欲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无上菩提须于当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中荐取。”说完,五祖吩咐神秀再作一偈。但是,几天过去了,神秀再没有作出新的偈子来。
后来有一天,慧能在碓坊舂米,听到外边有位童子在诵神秀的偈子,便上前打听,于是童子就把五祖吩咐大众作偈以及让大众梵香礼拜神秀之偈的事一一告诉了慧能。慧能听了,便央求童子道:“上人,我也要诵此偈,与秀上座结来生缘。自从我来到这里,我就一直舂米,八个多月,没有到过堂前,请上人引我到写有神秀偈子的廊壁前礼拜。”
于是,童子引慧能来到偈子前。慧能说:“我不识字,还请上人念给我听。”当时,江州别驾张日用正好在旁,便高声为慧能念诵那首偈子。
慧能听了,就说:“我也有一首偈子,请别驾给我写上。”别驾了听了,非常惊讶“你这个舂米的,也能作偈子,真是希有!”慧能正色道:“欲学无上菩提,不可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没有意智。若经人,即有无量无边罪。”别驾听了,连忙谢罪道:“汝念偈子,我给你写。如果你将来得法了,不要忘了要先度我。”于是慧能念偈道: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偈子刚写完,大众无不惊愕。五祖见众人如此,担心有人伤害慧能,于是用鞋掌把慧能的偈子抹掉了,并且说“亦未见性”。众人见五祖这么说,也就不以为意。
传得衣钵
第二天,五祖私下来到碓坊,见慧能腰间挂着石头舂米,说道:“求道之人,为法忘躯,就应当象你这个样子”。并问道:“米舂熟了吗?”慧能回答道:“米熟久矣,犹欠筛在。”五祖于是用拄杖在碓头上敲了三下便离开了。慧能领会了五祖的意思,便于当天晚上三更的时候,偷偷地来到五祖的丈室。五祖用袈裟将慧能围起来,以免他人发现,并且给他讲解《金刚经》。 当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慧能豁然大悟。原来一切万法不离自性!慧能一连说了五个何期,以表达自己悟道时的惊喜和见地:
当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慧能豁然大悟。原来一切万法不离自性!慧能一连说了五个何期,以表达自己悟道时的惊喜和见地:
“何期自性本自清净!
何期自性本不生灭!
何期自性本自具足!
何期自性本无动摇!
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五祖知道慧能已经大悟,便将顿教法门以及祖师衣钵传付给慧能,说道:“诸佛出世为一大事,故随机大小而引导之,遂有十地、三乘、顿渐等旨,以为教门。然以无上微妙、秘密圆明、真实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叶尊者,展转传授二十八世。至达磨届于此土,得可大师承袭,以至于今,今以法宝及所传袈裟用付于汝。善自保护,无令断绝。听吾偈曰:
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
无情既无种,无性亦无生。”
慧能禅师跪受衣法之后,问道:“法则既受,衣付何人(法我已经受了,将来这祖衣该交付给谁呢)?”
五祖回答说:“昔达磨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若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
慧能禅师又问:“当隐何所?”
五祖答道:昊臣粗梗龌崆也亍!?
说完,五祖便亲自把慧能连夜送到九江驿。临行前,五祖又嘱咐慧能:“以后佛法将通过你而大兴。你离开黄梅后三年,我将入寂。你赶快往南方走,好自为之。不要急于出来弘法。这当中你会有劫难。”
南下避祸
慧能禅师再一次顶礼五诅,然后发足南行,不到两个月就到了大庾岭。
五祖送走慧能后,连续好几天没有上堂。众人都很疑惑,老和尚是不是生病了, 于是纷纷前去问安。五祖告诉他们说:“我没有病,祖师的衣钵和法脉已经传到南方去了!”众人大惊,问道:“谁得到了衣钵?”五祖回答说:“能者得之。”
于是纷纷前去问安。五祖告诉他们说:“我没有病,祖师的衣钵和法脉已经传到南方去了!”众人大惊,问道:“谁得到了衣钵?”五祖回答说:“能者得之。”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此后便有了数百人前往南方追杀慧能禅师欲夺取衣钵的一连惊心动魄的故事。为了避免不测,慧能禅师一度在猎人队混了长达十五年之久。此后,因缘成熟了,慧能禅师才来到广州法性寺,在印宗法师的座下剃度,开始了他辉煌的弘法生涯。
在慧能禅师之前,禅宗一直是单传。自慧能禅师以后,禅宗很快在大江南北盛传开来,并形成了“一花五叶”的繁荣局面。慧能禅师的弟子很多,据《坛经》记载,有一千多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法海、法达、智常、志彻、神会等。禅宗史上非常有影响的青原行思、南岳怀让和南阳慧忠等大禅师,
也都是慧能禅师的法嗣。
慧能禅师入寂于先天元年(712),春秋七十六。他生前的主要讲法,由弟子法海整理成书,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读到的《坛经》。在佛教史上,中土人的著述,被称之为经的,唯慧能禅师一人。
慧能的学说
在思想体系上,慧能的学说有三根支柱。一是世界观上的真心一元论,即真如缘起论。二是解脱论上的佛性论;三是宗教实践上的顿悟思想。真心、真如又称佛性、法性、实性、自性、本性、法身、本心等等。慧能认为不管南北西东、尊卑贵贱,人人皆有佛性,佛性常清净;又认为于自性中,万法皆见;一切法自在性,名为清净法身。如此等等,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说明真如就是永恒的、绝对的、最高的精神实体,同时也是宇宙实体、世界本原。慧能肯定这种实体、本原,而认为此外的万事万物都是虚幻的、空的。 这种真心一元论或真如缘起论是慧能的思想核心,是其佛学的理论基础。其他两条支柱都是由此派生的。例如解脱论上的佛性论,就建基于人人皆有佛性。由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所以成佛之道,不假外修,更无须到西天去拜求,只要“直指人心”,便可“见性成佛”。这一点又决定了慧能教派在宗教实践上主张顿悟。因为人人都有佛性,只是迷人自不知见。去迷见性,只在一念之间。一念善,智慧即生。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如果这一念未到,纵使你勤修苦炼,“时时勤拂拭”,也是徒劳的。慧能佛学的特点还反映在他对禅和净土的独特看法上。传统的禅法,主张静坐敛心,慧能则认为在任何时刻的行、住、坐、卧、动作、言谈中,也可体会禅的境界。北宗禅继承传统禅学观点,教人静坐看心,以为那样将心境分为两截,不能契自心性而生智慧。慧能却教人只从无念着手,并不限于静坐一途。
这种真心一元论或真如缘起论是慧能的思想核心,是其佛学的理论基础。其他两条支柱都是由此派生的。例如解脱论上的佛性论,就建基于人人皆有佛性。由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所以成佛之道,不假外修,更无须到西天去拜求,只要“直指人心”,便可“见性成佛”。这一点又决定了慧能教派在宗教实践上主张顿悟。因为人人都有佛性,只是迷人自不知见。去迷见性,只在一念之间。一念善,智慧即生。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如果这一念未到,纵使你勤修苦炼,“时时勤拂拭”,也是徒劳的。慧能佛学的特点还反映在他对禅和净土的独特看法上。传统的禅法,主张静坐敛心,慧能则认为在任何时刻的行、住、坐、卧、动作、言谈中,也可体会禅的境界。北宗禅继承传统禅学观点,教人静坐看心,以为那样将心境分为两截,不能契自心性而生智慧。慧能却教人只从无念着手,并不限于静坐一途。
对于当时僧俗念佛愿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法门,慧能也另有一种看法。他强调“见自性清净,自修自作法身,自行佛行,自成佛道”。他曾对韶州刺史韦璩说:“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殊,见有迟疾。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使君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
慧能佛学在思想体系和传教方式上的特点,使其教派具有强烈的平民宗教色彩。他认为人人具有佛性,众生皆可成佛,打破了贵族、官僚对成佛作祖的垄断。他把人人向往的天堂从遥远的西方搬到每人的心中,同时又把修行的方式尽量简化,革去了繁琐的仪式。甚至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无异于拓宽了进入天堂的途径,自然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他肯定“真如”的真实性、永恒性,反对一切皆空的颓废虚无思想,符合新兴庶族地主阶级要求进取并保护既得利益的愿望,因而最受这个阶层的拥护、支持。但他又认为功德不在于造寺、布施、供养,而在于自性清净平直,不轻视一切人。这显然是有利于贫贱的劳动人民,不利于显贵的剥削者的。慧能的理论能够为劳动人民着想,其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传教方式又适应了贫苦人民的需要,所以他的教派又吸引了大量下层人民。所有这些,都是对传统佛教的巨大变革,对旧有的贵族化教派的严重挑战。实际上,慧能以一个出身贫贱的“獦獠”,居然登上教主的宝座,这一事实本身就富有向传统决裂的意味。以后他传教成功,声名远播,武则天、唐中宗先后下诏礼请他入朝,他都托疾不行,这固然有害怕北上受到守旧教徒迫害的因素,但也确实说明他与那些趋炎附势、以交结权贵为荣的大和尚们不同,反映出他和他的教派不同寻常,因而赢得了广大信众的尊敬和爱戴。理论上和方法上的巨大优势,使得慧能的信徒迅速扩大。他在韶州大梵寺升座说法,座下僧尼、道俗曾达1万余人,韶州刺史韦璩和诸官僚30多人、儒士30多人也来听他说法。他在韶、广二州传法行化30多年,及门弟子常不下三五千人。慧能10大弟子之一的志诚,原是北宗神秀的门下。神秀派他去慧能门下窃听说法旨意,但志成听了慧能说法,认为比神秀说得明白、深刻,容易理解,便主动说出了受命前来刺探虚实的真情,不愿离去,成了慧能门下的大弟子。慧能另一大弟子神会,生性聪明,自幼学贯群经、老庄,后又留心释教,出家后讽诵佛经,易如反掌。年14岁,听说慧能大师在曹溪盛扬佛法,学者如百川赴海,于是不远千里,前来参拜。交谈不久,就为慧能折服,投在门下,成为慧能的神足。这些事例,都说明慧能的崇高威信以及他的教派的巨大号召力。
慧能传法不立文字,全凭口讲。由于他使用当时日常通行的口语,又善用生动的比喻,娴熟运用朴素的辩证法,所以他的讲授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效果很好。譬如他解释定和慧的关系,说:“定慧犹如何等?如灯光。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把定和慧的相互关系说得明白透彻。又如他启发弟子正确地对待念经,说:“心行转《法华》,不行《法华转》;心正转《法华》,心邪《法华》转”。又说:“空诵但循声,明心召菩萨。”深入浅出地说明了诵经必须用心专一的道理。
慧能的弟子法海把他平生授法、与弟子们问答及临终时嘱咐的话记录下来,辑录成书,奉为经典,称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或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简称《坛经》。坛是指慧能平时授法的法坛。慧能的门徒把慧能看得像佛一样,他的法言就像佛经一样,所以叫做《坛经》。中国僧人的著作被称为“经”的,《坛经》是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慧能死后,其门徒传授《坛经》,师师相承。若无《坛经》,即无禀受,就不被承认为南宗弟子。可见《坛经》在中国禅宗史上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影响
禅无所不在,它即是一种直接潜入生命内核,超越物我,回归到人与宇宙自然的本真,以体验到生命本原的修行方法;同时又是通过这种方法以达到的一种澄明宁静、大彻大悟的心灵境界。
慧能大师是禅宗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国禅宗的正式建立者。大师被尊为禅宗六祖,是唐代著名佛教改革家。他出身寒微,不识文字,一生涵濡着平民性格,拒绝征诏,疏远官禅,始终保持了山林佛教的特色。他凭着天纵神悟,闻经起信,于五祖弘忍处,得传祖心,后至曹溪,大阐顿教法门,接化天下学人,成为中国禅宗的实际创始人。
慧能生活的时代,正是唐代政治文化走向繁荣的时期,云蒸霞蔚,异彩纷呈,也是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成熟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恢宏开放的思想文化氛围中,慧能不仅沿着达摩以来开拓的禅学中国化的道路
进一步发展了心性之学,而且还在贯通大乘佛教学说的基础上融摄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之学,包前孕后,独步古今,使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渐兴起的中国禅宗,至此而真正创宗立派,独立门庭,成为中国佛教隋唐八大宗之一。
慧能创立禅宗是佛教史上一次空前大改革,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第一,他大胆破除佛祖 的权威,不承认有所谓外在的佛,认为佛就在本心中。第二,他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这与儒家“人皆可为尧舜”的性善论相通。慧能之后,禅宗更进一步向儒家靠拢,竭力与儒家的以教悌为人之本的伦理学说相调和,写了大量论教的著作,从而促使了佛教 的进一步儒学化。第三,他不但主张人人都可以成佛,而且主张不用背诵佛经,不需累世修行,只要认识本心,就能成佛,即所谓“顿悟成佛”,从而不但迎合了上层统治者和士大夫的需要,而且也为下层人民信佛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第四,他在宣传“顿悟成佛”的同时,还提介自由任运的生活方式,促使禅宗生活的平民化、世俗化。慧能的三传弟子怀海禅师,更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宗佛,并将这一宗佛写进了《百丈清规》,从而对后世禅寺的建设及其劳动自养制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禅宗得以在中国迅速传播、广泛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慧能作为在我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其思想包含着的哲理和智慧,至今仍给人以有益的启迪,并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
慧能的五大弟子
即使在慧能最亲近的弟子中,也只有五个学生是最为独出的,现在我们简单的一一介绍如下:
①南岳怀让(公元六七七——七四四)
他是陕西金州人,俗姓杜。十五岁出家时先学律宗,曾潜心于律藏,后来不满所学,要再求深造;便到嵩山去拜慧安为师。慧安告诉他许多基本的佛理,并介绍他去见慧能。当他到了曹溪,慧能便问:“你是从那里来的”?
他回答:“从嵩山来”?
慧能又问:“来的是什么东西?是怎么来的”?
他回答:“说他是东西,就不对了”。
慧能再问:“是否还须加以修证呢”?
他回答:“我不敢说不可以修证,但可以说决不会污染”。
于是慧能便赞美说:“就是这个不会污染的,乃是佛菩萨要我们留心维护的,你的看法正好和我的相同”。
怀让便在慧能门下,跟随问学了十五年。在这段时期,他探微寻幽,极有心得。后来便到了南岳,大大的宏扬禅学。他的弟子中最有名的就是马祖道一,在后面我们将会详细介绍。
②青原行思(死于七零四年)
他是江西吉州人,俗姓刘。身世不明,只知道他从小出家,赋性沉默。在他第一次见慧能时便问:“我们要怎样才不致于落入相对的层次中”?
慧能反问说:“你最近做了些什么工夫”?
他回答:“我连圣谛也没有修过”。
慧能又问:“那么你的工夫究竟达到那一个层次呢”?
他回答:“我连圣谛也不修,还有什么层次可言”。
慧能被他的见地所深深的感动,认为他是学生中最有成就的一个。后来他被派到吉州青原山去大宏禅法,发扬了慧能的道统。据记载他只有一位杰出的弟子,就是石头希迁。虽然只有这么一位,但已经够了,正如他自己说:“众角虽多,一麟足矣”。
③永嘉玄觉(公元六六五——七一三年)
他以证道歌闻名。他是浙江永嘉人,俗姓戴。初学天台宗,曾潜心于禅观,在这方面已有特殊的成就。后来由于几位朋友的激励,便到慧能处印证所学。初见慧能时,他绕着慧能走了三圈,举着手中的锡杖,直立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慧能考问他说:“一个和尚要具有小乘的三千种威仪,和大乘的八万种戒行,请问你是从那儿来的,居然如此傲慢无礼”。
他不是理慧能的问话,却说:“人的生死只在呼吸之间,万物的变化是很迅速的,我顾不了这么多”。
慧能又说:“既然你担心生死无常,那么你为什么不证取不生不灭的大道,去断除无常迅速的烦恼呢”!
他回答:“真正能体认,大道本是无生无灭的,真正能了断,万物也本是无迟速可言的”。
他这种把体和用合成一征的见解赢得慧能的连声赞叹。于是他便按照礼展出向慧能行礼,然后就要告诉离去,慧能便说:“为什么这样匆忙的又要回去呢”?
他回答:“我根本就示曾动过,那里谈得上匆忙”!
慧能又问:“谁知道你未曾动过”?
他回答:“这是你自己产生的分别观念啊”?
慧能便说:“你已完全懂得无生的意思了”。
他又反驳说:“既然是无生,那里还有意思可言呢”。
慧能回答:“如果无生没有意思,叫人如何能分别它呢”?
他又说:“分别观念本身是没有意思的”。
慧能不禁连声赞叹,并劝玄觉留宿一夜,当时的人例称他为“一宿觉”。
④南阳慧忠(公元六七七——七七五年)
虽然我们找不到慧忠何时在慧能门下求道及开悟的记载,但大家都公认他是慧能的五大弟子之一。据我们所知,他在慧能处印证了后,便到南阳的白崖山上渡了四十余年,从未离山一步。直到公元七六一年,他才被肃宗邀到京城,尊为国师。在某次法会上,肃宗问了很多问题而他却不看肃宗一眼,肃宗生气的说:“我是大唐的天子,你居然不看我一眼”?
他便问说:“君王可曾看到虚空”?
肃宗回答:“看到”。
于是他便说:“那么请问虚空可曾对你眨过眼”。
这一问,问得肃宗无话可说。
慧忠是一位非常严厉的老师,这可以从他对付门人耽源的故事中看出。有一天,慧忠的一位年青朋友,名叫丹霞的,来找他。这时正好慧忠在小睡,丹霞便问耽源说:“国师是否在”?
耽源只是刚学了一点禅理,便卖弄的说:“在是在在的,只是不会客”。
丹霞便说:“啊!你答得太深奥了”。
耽源更故意说:“即使你有佛眼,也看不到他”。
丹霞不禁叹着说:“真是龙生龙,凤生凤”。
后来慧忠醒了,耽源便把丹霞来访的经过告诉他。那料慧忠听后,便打了耽源二十棒,并把他逐出庙门。当丹霞听到慧忠的作法后,深为佩服说:
“真不愧为南阳国师啊”!
这一则公案对我们学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初学禅的人,正像三岁小孩玩刀片一样,要想用刀片割任何东西,但结果却割破了自己的手。自从这个痛苦的经验以生,使耽源变得更为聪明,后来便成为慧忠的承继者。
⑤荷泽神会(公元六七零——七五八年)
虽然神会在禅宗的思想传统上并不重要,但在维护慧能的法统,以及使禅宗通俗化这点上,却是后无来者。因为由于他的充沛活力和坚苦的奋斗,才使得提倡顿悟的南禅,压倒了渐修的北禅。我们在这里介绍有关他和慧能的一些有趣故事。
神会是湖北襄阳人,俗姓高。在他十三岁那年便去参拜慧能。慧能问:“你千里跋涉而来,是否带着你最根本的东西,如果带来了,那么你应该知道它的主体是什么体?你说说看”。
神会回答说:“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无住,它的主体离不了开眼即看”。
慧能不禁赞叹说:“你这小和尚,词峰倒也敏利”。
接着神会又反问说:“师父坐禅时,是见或是不见”。
慧能便拿棒子敲了神会三下说:“我打你,是痛或是不痛”。
神会回答说:“我感觉得又痛,又不痛”。
慧能便说:“我是见,也是不见”。
神会又反问:“怎么是又见,又不见呢”?
慧能便说:“我见,是因为常见自己的过错;我不见,是因为我不见他人的是非善恶。所以是见,又是不见。至于你说是痛,又是不痛,如果是不痛的话,那么你便像木石一样的没有知觉;如果是痛的话,那么你便像俗人一样会有怨愤之心。我要告诉你,见和不见都是两边的执着,痛和不痛都是生灭的现象,你连自性都摸不清楚,居然敢作弄人”!
神会听了之后,大为惭愧,立刻向慧能行礼,悔谢,以后便成了慧能最虔诚的信徒。
有一天,在一个颇为正式的法会上,慧能向大家说:“我这里有一个东西,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你们是否认识呢”?
神会站出来说:“它是诸佛的本源,是神会的佛性”。
慧能批评说:“我已很清楚的告诉你它是无名无字的,你偏要叫它作本源和佛性。将来你即使有点成就,也只是咬文嚼字的知解徒罢了”。
这话果然说对了,神会后来正是如此。
在公元七一三年,慧能宣布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当时在场的,除了法海等人外,在五大弟子中,只有神会一人。他们听到慧能将要逝世,都放声大哭,只有神会默然不语,也不哭泣。慧能便说:“只有神会一人超越了善恶的观念,达到了毁誉不动,哀乐不生的境界。你们这些人在山上数年,究竟求的是什么道?你们今天哭泣究竟是为了谁?我很清楚自己究竟要到那里去。如果我对自己的死一无所知,我又如何能预先告诉你们。你们之所以哭泣,是因为不知我死后往那里去,如果知道了,便不会哭泣。你们要知道,法性是不会生灭去来的。”
禅的故事
人有南北, 佛性岂然?
咸亨中师自新州参谒五祖。祖问曰:“汝自何来?”
师曰:“岭南。”
祖曰:“欲须何事?”
师曰:“唯求作佛。”
祖曰:“岭南人无佛性,若为得佛?”
师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岂然?”
祖知是异人,乃诃曰:“着槽厂去。”
轮刀上阵
经八月,祖知付授时至,一日唤诸门人总来:“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来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 ”
菩提本无树
时会下七百余僧。上座神秀者,学通内外,众所宗仰,乃于廊壁书一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祖见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赞叹曰:“后代依此修行,亦得胜果。”师在碓坊,忽聆诵偈,知未了,因请别驾张日用于秀偈之侧,另书一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祖后见此偈曰:“此是谁作,亦未见性。”
米熟矣
次日,祖潜至碓坊,见师腰石舂米,语曰:“求道之人,当如是乎?」乃问曰:“米熟也未?」师曰:“米熟久矣,犹欠筛在。”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去。师即会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师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启祖言:
何期自性,本自清净;
何期自性,本不生灭;
何期自性,本自具足;
何期自性,本无动摇;
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祖谓师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遂传顿教及衣钵。云:“诸佛出世为一大事,故随机大小而引导之,遂有十地、三乘、顿渐等旨,以为教门。然以无上微妙、秘密圆明、真实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叶尊者,展转传授二十八世。至达磨届于此土,得可大师承袭以至于今,以法宝及所传袈裟用付于汝。善自保护,无令断绝。」
风动幡动
师一日思惟:“时当弘法,不可终避。”遂出至广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师讲涅盘经。因二僧论风幡义,一曰风动,一曰幡动,议论不已。师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众骇然,印宗知是五祖传人,延至上席,征诘奥义,因欢喜合掌,言:“某甲讲经,犹如瓦砾;仁者论义,犹如真金。”告四众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萨。”请出所传信衣,悉令瞻礼。于是为慧能剃发,愿事为师。
附录: 慧能的禅法思想
坛经之成立及其演变
慧能的禅法思想
根据《六祖坛经》,慧能在向信众说法中,主要强调以下思想:
(1)众生皆有佛性,皆可自修自悟
《六祖坛经》记述,慧能在韶州大梵寺登上高座,”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是说慧能向听众讲《摩诃般若经》的一切皆空和中道的思想,并且向信徒授”无相戒”。
那么,什么是无相戒呢?慧能的无相戒是以佛性为戒体、本源的大乘菩萨戒,也可称为”佛性戒”、”持心戒”。他把这种戒与传统的”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边誓愿学,无上佛道誓愿成”)、”忏悔”、”三归依”(归依佛、法、僧)融为一体,并且借助向众生授戒的形式,宣传众生皆有佛性,佛在每个人的自心,说”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人人皆可自修自悟。称此戒”无相”,不外乎有两种原因:一是表示此戒以”佛性”为体,而”佛性”是实相无相,”心”无相;二是授戒时仅传授象征佛性的戒体,而不传授包括”菩萨戒”的十重戒、四十八轻戒在内的”戒相”,所以称为无相戒。
强调自心佛性是戒体,是戒的清净本源;佛、法、僧三宝在每人的自性之中;教人坚定主观信仰,说自修自悟就可以成佛,就构成了慧能的无相戒的主要内容和特色。
(2) 提倡顿教法门和”识心见性”,
慧能的禅法理论有两大理论来源:一是大乘般若中观学说,他经常引用的经典有《摩诃般若经》、《金刚般若经》和《维摩经》(《净名经》);二是大乘涅盘佛性学说,常引用的经典有《大涅盘经》。他从般若学说吸收空观本体论和观察思考问题的方法论--二谛论和不二法门;从涅盘佛性学说中吸收人人皆可成佛的佛性论,然后巧妙地将二者加以变通融合,构成自己的禅法体系。
慧能通过向信众讲”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反复强调:(一)人人皆具有佛性本心,它本来清净,但被世俗”妄念”所掩覆,不得显现;(二)借助般若智慧观想主客观世界,促使各种执著妄念(情欲、世俗观念)断灭,做到”识心见性”,即真正体认自己的本有佛性,便能在精神上达到与真如佛性相契合的清净超脱(无念,无忆,无著)的境界,就是”一悟即至佛地”。在这里,他把”见性”、”无念”以及”般若三昧”(意为智慧禅定)等概念等同起来,是认为它们都是与真如佛性相契合的状态。”见性”是体悟真如;”无念”是契合真如的无为清净的精神状态;”般若三昧”是领悟真如,获得智慧的禅观境界。
慧能所说的”一悟即至佛地”,是顿时豁然开悟,是顿悟。他虽主张顿悟,但他又表示,佛法本身没有顿渐之分,只是人领悟佛法的素质有利钝之别。”迷自渐劝,悟人顿修”,是说没有领悟自心本有佛性的人,应当循次勉力,而一旦体悟自性,便可顿修成佛。
(3)”无念为宗”--寄坐禅于自然无为和日常生活之中
戒、定、慧是佛教的三学,包笼全部佛法。从整体上看,三者有机联系,构成佛法的全体。但三者又各有相对的独立性,各有自己的内容和特色。对此,慧能似乎也承认,但他提出一个前提,即对于没有觉悟的人来说才有戒、定、慧的差别,而对觉悟自性的人来说,三者皆为自性,是自性的不同定位的名称。
北宗神秀对戒定慧的解释是:”戒”是”诸恶不作”,”慧”是”诸善奉行”,皆是对行为的约束和规范,只有”自净其意”的”定”,才是制约人的心理活动的。针对此说,慧能提出:”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乱自性定,心地无痴自性慧。”是说”心地”无非、无乱、无痴,指的不是三个物件,恰恰指的是”佛性”本身。所谓”自性戒”、”自性定”、”自性慧”,无非是说佛性本身就是戒、定、慧,它们并非存在于人的心性之外,而是本来为人的心性所有。他提出”定、慧不二”,认为不必”先定发慧”,实际更加重视智慧。
慧能明确地规定自己禅法是”立无念为宗”。所说的”无念”不是要求人们离群索居,闭目塞听,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念,而是照常生活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之中,照常从事各种活动,只是要求对任何事物、任何对象都不产生贪取或舍弃的念头,没有执意的好恶、美丑的观念。
按照”无念”的精神,修行者是否一定要依照固定的程式进行坐禅呢?当然不是。不论是出家还是在家,只要直探心源,自修自悟,对一切没有”执著”,那么,任何时候,无论是行住,还是坐卧,都可以看作是坐禅。他对禅定作出新的定义,说:”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何名为禅定?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可见,”坐”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坐”(打坐,结跏趺坐),而是”念不起”,亦即不起杂念、妄念;”禅”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禅”(禅定,静心思维),而是”见本性不乱”(”见”,意为显现,与本性相应),意即坚持清静自性(文中也称”内心”)不受外界干扰。”念不起”和”见本性不乱”或”内不乱”,皆是特种精神境界,无非是相信自己本具清净佛性,即心是佛,不受周围环境和任何事物的影响。
慧能倡导顿修顿悟、明心见性的禅法,在中国佛教史上掀起了一场不假他求、但明自心的革新。从慧能开始,“禅”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以往的禅定修行转化成一种在人心深处、贯穿于百姓日常生活的对于真实性的体悟。研究慧能佛教思想的资料主要是《坛经》一书,它是慧能弟子或再传弟子等所记载的慧能的言行录。中国僧人的说教被称为“经”,这在历史上是头一次,至今也独此一家。
坛经之成立及其演变
第一节 坛经的主体部分
《坛经》为慧能大师所说,弟子法海所集记,这是《坛经》自身所表明的。过去以明藏本《坛经》为惟一的《坛经》。到了近代,敦煌写本(斯坦因5475号,编入《大正藏》卷四八)发现了,日本的兴圣寺本大乘寺本等出版了,《坛经》的研究进入了一新的阶段。一般以敦煌本为现存各本中最古的本子。《坛经》(以敦煌本来说)是否慧能所说呢?胡适(1930年)在《神会和尚遗集》,以敦煌本为最古本,主要为神会(少部分为门下)所作。宇井伯寿(1935年)《第二禅宗史研究》,立场比较传统,除去《坛经》中的一部分,其余为慧能所说。关口真大(1964年)《禅宗思想史》,对宇井伯寿那种办法,不表同意,另从传说中的《金刚经口诀》,去研究慧能的思想,而以《坛经》为代表神会的思想。柳田圣山(1967年)《初期禅宗史书之研究》,以为“无相戒”、“般若三昧”、“七佛二十九祖说”,是牛头六祖慧忠所说,鹤林法海所记的。神会晚年,把他引入自宗,由门下完成,约成立于《曹溪别传》及《宝林传》之间(781—801年)。《坛经》到底是否慧能所说,法海所集所记?还是神会(及门下)所造,或部分是牛头六祖所说呢?我不想逐一批评,而愿直率地表示自己研究的结论。
东山门下的开法传禅
禅宗到了唐初,忽然隆盛起来;禅法的普遍传授,确是使达摩禅进入新阶段的重要因素。禅法传授的重大演变,如杜胐《传法宝纪》说:
慧可,僧璨,(脱一字)理得真。行无辙迹,动无彰记。法匠默运,学徒潜修。至夫道信,虽择地开居,营宇立(原误作“玄”)象。存没有迹,旌榜有闻。而犹平生授受者,堪闻大法,抑而不传。……及忍、如、大通之切,则法门大启,根机不择,齐速念佛名,令净心。密来自呈,当理与法。
据《传法宝纪》所说,弘忍以下,禅法开始为公开的、普遍的传授(这含有开宗立派的意思)。这种公开的传授,当时称之为“开法”、“开禅”,或称为“开缘”。在早期的禅学文献中,留下了明确的记录。属于北宗的,如《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金石续编》卷六)说:
忍传如。……垂拱二年,四海标领僧众,集少林精舍,请开禅法,……谦奶三让,久乃许焉。
垂拱二年(686年),离弘忍的去世(674年,或说675年)约十年。法如为弘忍弟子,是临终时侍奉在身边的一位。法如在嵩山少林寺开法,《传法宝纪》也说:“垂供中,都城名德惠端禅师等人,咸就少林,累请开法,辞不获免。……学侣日广,千里响会。”但法如开法不久,永昌元年(689年)就去世了。
法如去世后,在荆州玉泉度门兰若的神秀就起来开法接众,如《传法宝纪》说:
(神秀)然十余年间,尚未传达。自(法)如禅师灭后,学徒不远万里,归我法坛。遂开善诱,随机弘济。天下志学,莫不望会。
神秀开法传禅的盛况,也如《大通禅师碑》(《全唐文》卷二三一)说:
云从龙,风从虎;大道出,贤人睹,岐阳之地,就者成都;华阴之山,学来如市:未云多也!……升堂七十,味道三千,不是过也!尔其开法大略,则专念以息想,极以摄心。……持奉楞伽,递为心要。
神秀在玉泉开法的盛况,极为明确。《宋唐文》(卷九)“义福传”说:“神秀禅门之杰,虽有禅行,得帝王重之无以加者,而未尝聚徒开法也”(大正50·760中)。《宋僧传》说神秀没有聚徒开法,是与事实不符的,这大概是曹溪门下的传说!
与神秀同时,而多少迟一些的,有安州玄赜。玄赜也是弘忍门下,是弘忍临终时侍奉在侧、为弘忍建塔的弟子。玄赜的开法,如《楞枷师资记序》(大正85·1283上)说:
(安州寿山大和尚讳赜)大唐中宗孝和皇帝景龙二年,敕召入西京。便于东都广开禅法,净觉当即归依,一心承事。两京来往参觐,向(经十)有余年。
玄赜在景龙二年(708年),受则天的礼请,净觉就在那时归依。从参觐十有余年来说,大概720年前后,玄赜还在两京开法。净觉是《楞伽师资记》的作者,为玄赜的入室弟子。净觉继承了玄赜,也在两京开法。如净觉在开元十五年(727年)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李知非所作《经序》中说:
净觉禅师,比在两京,广开禅法。王公道俗,归依者无数。
神秀门下,《楞伽师资记》列举了普寂、敬贤、义福、惠福、——四位禅师。其中,普寂(开元二十七年卒)为神秀门下杰出的禅师。《南宗定是非论》说:“普寂禅师开法来数十余年。”(《神会集》290)《宋僧传》(卷九)“义福传”也说:“普寂始于都城传教二十余载,人皆仰之。”(大正50·760中)从法如到普寂(686—739年),北宗禅在两京开法的盛况,可说到了极点!
弘忍门下,还有智诜,也曾受到则天帝的礼敬,住资州德纯寺,长安二年(702年)去世。智诜的再传弟子无相,人称“金和上”(宝应元年去世),住成都净众寺。如《历代法宝记》(大正51·184下—185上)说:
无相禅师,俗姓金。……后章仇大夫,请开禅法,居净泉(众)寺,化道(导)众生。
金和上每年十二月、正月,与四众百千万人受缘,严设道场,处高座说法。
这是东山下净众寺一流。《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也说到“无住……游蜀中,遇金和上开禅,亦预其会。”并说这种开禅的法会,名为“开缘”(续14·278)。
被称为“南宗”的慧能门下,在京洛大开禅法的,是神会,如《南宗定是非论》(《神会集》283)说:
能禅师是的的相传付嘱人。已下门徒道俗近有数(应脱落“十”或“百”字)余人,无有一人敢滥开禅门。纵有一人得付嘱者,至今未说。
“一人得付嘱者,至今未说”,就是神会自己。在开元二十年(732年)左右,神会还没有开法。神会是天宝四年(745年),因兵部侍朗宋鼎的礼请而到东京(洛阳)的。天宝八年(749年),神会在洛州荷泽寺定宗旨,但法难就来了,如《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续14·277)说:
因洛阳诘北宗传衣之由,及滑台演两宗真伪,与崇远等持(原误作“诗”)论一会。……便有难起开法不得。
神会在被贬逐(753年)以前,还不曾开法。直到安禄山作乱,郭子仪收复两京(757年),神会才以六祖付嘱人的资格,大开禅门,如《历代法宝记》(大正51·185中)所说:
东京荷泽寺神会和上,每月作檀场,为人说法,破清净禅,立如来禅。
坛经的原始部分
弘忍以来,有公开的开法传禅。传禅的方便,彼此都有所不同,但有一共同的形式,那就是戒禅合一。第二章指出,道信法门的特色之一,是菩萨戒与禅法的结合。第四章中,曾列举南宗、北宗、净众宗、宣什宗——东山门下的开法情形;南宗与北宗,明显地达到了戒(佛性本源清净)与禅的合一。这是历史的事实,一代的禅风。了解一般开法的特性,就知道《坛经》也有一部分——大梵寺说法。这一部分,现有的《坛经》不同的本子,在次第上,文句上,虽有些也入,然分析其组成部分,是大体相同的。敦煌本的次第是:
善知识!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法。
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已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
善知识!总须自体与受无相戒。一时逐慧能口道,令善知识见自三身佛。
今既归依自三身佛已,与善知识发四弘大愿。
既发四弘誓愿讫,与善知识无相忏悔三世罪障。
今既忏悔已,与善知识受无要三归依戒。
今既自归依三宝,总各各至心,与善知识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
大梵寺说法部分,不是一般的说法,是公开的开法传禅,是与归戒、忏悔、发愿等相结合的。明藏本说:“于城中大梵寺讲堂,为众开缘说法。”(大正48·347下)“开缘”,正是开法传禅的别名。
宣什与净众宗的开法,没有详细的记录流传下来(《历代法宝记》有金和上开示三句的大意)。神秀有《大乘无生方便门》;神会有《坛语》;慧能有《坛经》的大梵寺说法部分。开法,是不止一次的。无论是神秀、慧能、神会或其他禅师,每次开法,特别是开示法门部分,不可能每次都是一样的。如每次同样,那就成为宣读仪轨,失去了开法的意义。《大乘无生方便门》(现有敦煌出土的,四种大同而又多少增减的本子,就是不同一次的开法,不同记录的例子)、《坛语》,都不是神秀与神会的著作,而是一次一次的开法,由弟子忆持其共通部分而记录下来的。慧能的开缘说法,想来也不止一次。现存的是以大梵寺开法为主(这应该是当时最盛大的一次),由门人忆持记录而成。
《坛经》现存各本的内容,含有其他部发,而不限于大梵寺说法的。然《坛经》的主体部分,即《坛经》之所以被称为《坛经》的,正是大梵寺的说法部分,如敦煌本《坛经》(大正48·337上)说;
慧能大于大梵寺讲堂中,升高座,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刺史遂令门人僧法海集记,流行后代,……说此坛经。
宋代禅者的意见,也正是这样。如宋道原于景德元年——1004年上进的《传灯录》卷五(大正51·235下)说:
韶州刺史韦据,请于大梵寺转妙法论,并受无相心地戒。门人记录,目为坛经,盛行于世。
《传法正宗记》,是契嵩的名著,嘉祐六年(1061年)上呈。卷六(大正51·747中—下)也说:
韶州刺史韦据,命居其州之大梵寺说法。……
其徒即集其说,目曰坛经。
契嵩曾写了一篇《坛经赞》,是至和元年(至和三年的前二年——1054年)所作,编入《镡津文集》卷三。所赞的《坛经》,内容,是:“定慧为本”、“一行三昧”、“无相为体”、“无念为宗”,“无住为本”、“无相戒”、“四弘愿”、“无相忏”、“三归戒”、“说摩诃般若”、“我法为上上根人说”、“从来默传分付”、“不解此法而辄谤毁”(大正52·663上—下)。契嵩所赞的《坛经》内容,就是大梵寺说法部分,次第完全与敦煌本相同。这是敦煌本《坛经》,为现存各本《坛经》中最古本的明证。古人心目中的《坛经》,是以大梵寺说法部分为主体的。所以现存的《坛经》,应分别为二部分:一、(原始的)《坛经》——“坛经主体”,是大梵寺开法的记录。二、“坛经附录”,是六祖平时与弟子的问答,临终付嘱,以及临终及身后的情形。二者的性质不同,集录也有先后的差别。在《坛经》的研究上,这是应该分别处理的。
《坛经》,尊称为“经”,当然是出于后学者的推崇。为什么称为“坛”——大梵寺说法部分,被称为“坛经”呢?这是由于开法传禅的“坛场”而来。如《传法宝记》说:“自(法)如禅师灭后,学徒不远万里,归我法坛。”《历代法宝记》说:“荷泽寺神会和上,每月作檀场,为人说法。”(大正51·85中)《坛语》也说:“已来登此坛场,学修般若波罗蜜。”(《神会集》232)当时的开法,不是一般的说法,是与忏悔、发愿、归依、受戒等相结合的传授。这是称为“法坛”与“坛场”(坛,古代或通写出为檀)的理由,也就是被称为《坛经》、《坛语》的原因。
坛,有“戒坛”、“密坛”、“忏坛”、“(施)法坛”。“戒坛”是出家人受具足戒的坛场;慧能、神会的时代,“戒坛”早已成立。开元中,又有“密坛”的建立,这是传授密法、修持密法的道场。礼忏有“忏坛”,如隋智顗所说、灌顶所记的《方等三昧行法》(大正46·945上)说:
道场应作圆坛,纵广一丈六尺……作五色圆盖,悬于坛上。
“道场”,是行道——忏悔、坐禅等处所。“坛”是道场的主要部分,是陈设佛像、经书,庄严供养的。依天台家所传,忏悔也与归依、受戒、坐禅等相结合。神会的《坛语》,说到“道场”,又说到“坛场”,这是忏悔、礼拜、发愿、受戒、传授禅法的地方。凡忏悔、受戒、传授密法,都有“坛场”。唐代禅者的开法,也在坛内进行授戒、传禅,这就是“法坛”或“施法坛”了。
上来的引述,主要为了证明:东山门下的禅法,取公开的、普遍的传授方式,与忏悔、归戒等相结合。所以仿照“戒坛”(或“忏坛”)而称之为“法坛”、“施法坛”。慧能在大梵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弟子们记录下来,就称为《坛经》或《施法坛经》。这就是《坛经》的主体,《坛经》的原始部分。
第二节 敦煌本坛经的成立
慧能在大梵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传说由弟子法海记录,为《坛经》的主体部分。这在慧能生前,应该已经成立了。等到慧能入灭,于是慧能平日接引弟子的机级缘,临终前后的情形,有弟子集录出来,附编于被称为《坛经》的大梵寺说法部分之后,也就泛称为《坛经》。这才完成了《坛经》的原型,可称为“曹溪原本”。
以现存《坛经》本来说,敦煌本最古。但敦煌本已不是《坛经》原型,而有过补充、修改,这是古人所曾经明白说到的。
荷泽门下的坛经传宗
《坛经》是先后集成的,并有过修改过补充,但《坛经》代表了慧能南宗的顿禅,一向是大家(禅者)所同意的。到近代,才有神会或神会门下造《坛经》的见解。其中一项文证,是韦处厚(死于828年)所作《兴福寺内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全唐文》卷七一五)所说:
秦者曰秀,以方便显。
洛者曰会,得总持之印,独曜莹珠。习徒迷真,橘枳变体,竟成坛经传宗,优劣详矣!
吴者曰融,以牛头闻,径山其裔也。
楚者曰道一,以大乘摄,(大义)大师其党也。
韦处厚叙述当时的禅宗四大派,说到在洛阳的是神会。神会的习徒,“竟成坛经传宗”这确实是说到了《坛经》与神会门下的关穑熬钩晌尘凇保鞘裁匆庖澹坑τ谐浞值睦斫猓挪换嵋蛭蠼舛肴敕欠恰u饩浠埃凇短尘返亩鼗捅局校⑾至嗣魅返慕馑担缢担?br> 刺史遂令门人僧法海集记,流行后代。与学道者,承此宗旨,递相传授,有所依(原作“于”)约,以为禀承,说此坛经。(大正48·337上)
若论宗旨,传授坛经,以此为依(原作“衣”)约。若不得坛经,即无禀受。须知法处年月日姓(原作“性”)名,递(原作“遍”)相付嘱。无坛经禀承,非南宗弟(原作“定”)子也。未得禀承者,虽说顿教法,未知根本,终(原作“修”)不免诤。(大正48·342上)
大师言:十弟子!已后传法,递(原作“仰”)相教授一卷坛经,不失本宗。不禀受(原作“授”)坛经,非我宗旨。如今得了,递(原作“迎”)代流行。得遇坛经者,如见吾亲授。(大正28·343下)
大师言:今日已后,递(原作“迎”)相传授,须有依约,莫失宗旨。(大正48·344下)
此坛经,……悟真的岭南曹溪山法兴寺,见今传受此法。如付此(原作“山”)法,……持此经为依(原作“衣”)承,于今不绝。……不得妄付坛经。(大正48·345中)
敦煌本《坛经》,如上所引述的,一再明确地说到:“若不得坛经,即无禀受”;“不禀受坛经,非我宗旨。”在传法同时,要传一卷《坛经》。《坛经》不只代表慧能的宗旨,又是作为师弟间授受的“依约”(依据,信约);凭《坛经》的传授,以证明为“南宗弟子”的。《坛经》是被“传”被“付”的,是传授南宗宗旨的“依约”,这就是“坛经传宗”。
圭峰《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上)说:“荷泽洪州,参商之隙”(大正48·401中)。洪州——道一门下,荷泽——神会门下,当时是有些嫌隙的。韦处厚为大义禅师作碑铭;大义是道一弟子,所有对神会门下的批评,正代表道一门下的意见。照韦处厚的碑文所说:神会“得总持之印,独曜莹珠”,对神会是存有崇高敬意的。即使神会不是独得慧能的正传,也是能得大法的一人(那时的洪州门下,还不敢轻毁神会)。但神会的“习待,迷真”向俗,如“橘逾淮而变枳”一般,看起来,还是弘传神会所传的南宗顿禅,而实质上是变了,竟然变成用“坛经”来作为“传宗”的依约。失去传法——密传心印的实质,而换来传授《坛经》的形式。所以神会是“优”越的,神会的习徒是低“劣”的,优劣是非常明白了。这是当时道一门下对神会门下的责难,因而靠民嫌隙。神会门下未必专重传授《坛经》的形式,然以传授《坛经》为付法的依约,从敦煌本《坛经》看来,是确实如此的。神会门下应用《坛经》为付法的依约,所以在当时手写秘本的《坛经》上,加上些禀承、依约的文句。依大义禅师碑铭,说神会门下对《坛经》有什么改变,那只能证明是“坛经传宗”这部分。
神会门下为什么要用《坛经》来作“传宗”的依约?从迹象看来,当时神会门下,在禅法的传授上,有一重大困扰。起初,神会责难北宗门下,确定慧能为六祖。当时最有力的一着,就是依衣,如《南宗定是非论》(《神会集》281—282、284—285)说“:
经今六代,内传法契以印证心,外传袈裟以定宗旨。从上相传,一一皆与达摩袈裟为信。其袈裟今见在韶州,更不与人。余物相传者,即是谬言。
法虽不在衣上,表代代相承,以传衣为信,令弘法者得有禀承,学道者得知宗旨不错谬故。
神会以弘忍传衣给慧能,证明慧能为六祖。袈裟是“信衣”,是证明“得有禀承”、“定其宗旨”的,然而神会自己,慧能并没有传衣给他。神会没有传衣为禀承,那怎能证明是代代相传的正宗?在神会责难秀门下的时候,应该已多少感觉到了。所以在定宗旨的大会上,不能明说自己得慧能的传授,只能隐约地说:“能禅师已后……传授者是谁?(会)和上答:已后应自知。”“纵有一人得付嘱者,至今未说。”(《神会集》286、283)四川的净众、保唐门下,看透了这一问题,因而提出意见,神会没有传承慧能的正宗,如《历代法宝记》(大正51·185中—下)说:
会和上云:若更有一人说,会终不敢说也。为会和上不得信袈裟。
远法师问(神会)禅师:上代袈裟传不?会答:传。若不传时,法有断绝。又问:禅师得不?答:不在会处。
有西国人迦叶,贤者安树提等二十余人,向会和上说法处。问:上代信袈裟,和上得不?答:不在会处。
神会在动扰中成功(天宝战乱以前,神会还没有开法),没几年又在动乱中去世。到了神会门下,没有信袈裟,那与北宗禅师们有什么差别?而四川的保唐门下,正传说衣在无住处,证明慧能的法统在四川,这应该是神会门下最感困扰的事了!在这种情形下,发生了“坛经传宗”的事实。当时,《坛经》是手写秘本。在传法付嘱时,附传“一卷坛经”,“以此这依约”。对外宣称慧能说衣不再传了,以后传授一卷坛经以定宗旨。《坛经》代替了信袈裟,负起“得有禀承”,“定其宗旨”的作用。这就是“坛经传宗”的意义,也就是道一门下责难荷泽门下的问题所在。神会死于762年,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敕定神会为七祖。《历代法宝记》约作于775年。大义禅师死于818年。所以神会门下修改《坛经》,以《坛经》为传宗的依约,大抵在780—800年间。
与“坛经传宗”有关的,敦煌本还有一大段文(大正48·344中—下);
此顿教法传受,从上已来,至今几代?六祖言:初传受七佛,释迦牟尼佛第七。大迦叶第八,阿难第九,……南天竺国王子第三子菩提达摩第三十五。唐国,僧慧可第三十六,……慧能自身当今受法第四十,(原误作“十四”)
大师言:今日以后,递相传受,须有依约,莫失宗旨。
说到传法的统系,经律旧有各种不同的传承。与禅宗传法统系相关的,有三:一、佛陀跋陀罗——觉贤三藏,来中国传禅,在庐山译出《达摩多罗禅经》(约411年译出),慧观作序(见《出三藏记集》卷九)。《禅经》(及经序)叙述禅法的传承,说到大迦叶、阿难、末田地、舍那婆斯、优波崛(五师)、婆须蜜、僧伽罗叉、达摩多罗、不若蜜多罗。二、后魏吉迦夜等(约472年顷)传出的《付法藏传》六卷,也是从大迦叶等五师起,到师子尊者止,共二十四人。三、梁僧祐(518年卒)撰《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有“萨婆多部记目录”,中有两种大同小异的传说。1.“旧记”所传:从大迦叶到达磨多罗(后五师,都是《禅经序》所说的),共五十三世。2.“长安城内齐公寺萨婆多部陀跋跎罗师宗相承略传”,从阿难第一起,到僧伽佛澄,共五十四世。比“旧记”所说,在达摩多罗后,又增出四人。僧祐是律师,所以看作律的传承,其实与佛陀跋陀所传有关,是参照《付法藏因缘传》而补充集成的。这三种(四说)法统谱系,为后代禅者的主要依据。
自道信、弘忍以来,禅风大盛,达摩以来的传承,也就自然地传说出赤。统论禅宗法统说的发展,略有三个时期。第一,弘忍门下的早期传说(680—?):中国方面,从菩提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到神秀,或说慧能。天竺方面,引《达摩多罗禅经》,以说明远承天竺。代表北宗的是这样,如《唐中岳沙门释法如行状》、《传法宝纪》。代表南宗的神会,也是这样,如《南宗定是非论》(《神会集》294—295)说:
和上答:菩提达摩西承僧伽罗叉,僧伽罗叉承须婆蜜,须婆蜜承优波崛,优波崛承舍那婆斯,舍那婆斯承末田地,末田地承阿难,阿难承迦叶,迦叶承如来付。唐国以菩提达摩而为首,西国以菩提达摩为第八代。西国有般若波罗蜜多罗承菩提达摩后,唐国有慧可神师承菩提达摩后。自如来付,西国与唐国,总经有一十三代。
神会的东西十三代说,只是将菩提达摩以来的六代,与《禅经》说相结合。《禅经》说:“尊者达摩多罗,乃到不如蜜多罗。”神会说:“西国有般若(与“不如”音相近)蜜多罗承菩提达摩后,唐国有慧可禅师承菩提达摩后”;这可见神会是以达摩多罗为菩提达摩的。禅者都注重修持,对精思密察的法相,翔正确实的历史,是他们所忽略的。禅者的传法统系(古代的),虽引用古说,但没有经过严密的考订,而是在充满热心的传说中,逐渐发展而来的。西国的传承,引用《禅经序》;中国的传承,菩提达摩以来,已有六代。这是当时禅者的一般意见,神会也只是采用当时的传说而已。神会依《禅经序》,以达摩多罗为菩提达摩,可说错得有点意义。如《出三藏记集》卷九“修行地不净观经序”(慧观所作)(大正55·66下—67上)说:
昙摩多罗菩萨与佛陀斯那,俱共咨得高胜,宣行法本。
昙摩(多)罗从天竺来。
又,《达摩多罗禅经》“序”(慧远所作)(大正15·301中)说:
达摩多罗与佛大先,其人西域之后,禅训之宗。
达摩多罗阖众篇于同道,开一色为恒沙。其为观也,明起不以生,灭不以尽,虽往复无际,而未始出于如。故曰:色不离如,如不离色;色则是如,如则是色。佛大先以为:澄源引流,固宜有渐。
佛陀跋陀罗(觉贤)的禅学,含有两个系统:一、罽宾(北方)的渐禅,是佛大先(即佛陀斯那)所传的。二、天竺(南方)来的顿禅,是达摩多罗所传的。“色不离如,如不离色”,是直观一切法法皆如的。达摩多罗是菩萨,是天竺而不是罽宾,是顿禅而不是渐禅,这是引起禅者以达摩多罗为菩提达摩的原因吧!
第二,西天二十八祖说形成时期(约730—?):初期禅者的粗略传说——西国七代说,略加注意,就会发觉到一千多年而只有七代,决定是不妥当的,于是二十八代(或二十九世)说兴起。二十八世与二十九世,原则是一样的,都是《付法藏传》与《禅经序》的结合(梁僧祐《出三藏记集》所出的二说,用意相同)。在《付法藏传》的基础上,加上《禅经序》的(除去迦叶、阿难、末田地——三师,因为是重复的)舍那婆斯、优波崛、婆须蜜、僧伽罗叉,及达摩多罗(或作菩提达摩,菩提达摩多罗)——五师。从(《付法藏传》的)迦叶到师子尊者——二十四世;加(《禅经序》的)舍那婆斯等五世,成二十九世说。如李华所作《左溪大师碑》(左溪玄朗卒于754年)说:“佛以心法付在迦叶,此后相承,凡二十九世。至梁、魏间,有菩萨僧菩提达摩禅师。”(《全唐文》卷三二o)《历代法宝记》,也用二十九世说,为成都保唐宗的传说,约作于775年顷。二十八世说,是流行于京、洛的神会门下所说的。或不取末田地,或没有弥遮迦,所以为二十八世。如荷泽门下别派(718年)所作的《曹溪大师别传》,立二十八祖。《坛经》敦煌本,从七佛到慧能,共四十世。如除去七佛,中国的慧可到慧能,那末从迦叶第八到菩提达摩第三十五,也正是二十八。荷泽神会门下,为了“传宗”而对《坛经》有所添糅;二十八世是合于荷泽门下所说的。这一二十八世说,一直为荷泽宗所采用。圭峰(813年)造《圆觉经大疏钞》,也还是采用这一说。当时虽有二十九及二十八世说,但“二十八”数渐为后代的禅者所公认。
第三,西天二十八祖改定时期:二十八世或二十九世说,流行于八世纪。然而如注意到内容,就会发现重大的谬误,原来《付法藏传》的商那和修与优波罗崛多,与《禅经序》的舍那婆斯及优波崛,只是译语不同,并非别人。所以旧有的二十八祖说,以商那和修,优波罗掘多为第三、第四,舍那婆斯、优崛为第二十八祖说,以商那和修,优波罗掘多为第三、第四,舍那婆斯、优波崛为第二十四、二十五,看作不同时代的禅师,那不能不说是错误了。贞元十年(801年),金陵沙门慧炬(或作智炬,法炬)作《宝林传》十卷,沿用了二十八代的成说,而加以内容的改变。对《禅经》的舍那婆斯与优波崛,因重复而删去了。婆须蜜,参照僧祐的传说,而提前为第七祖。僧伽罗叉,被解说为旁支,而从二十八世中除去。《宝林传》改写的后四祖为: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罗
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
婆舍斯多,据梵名波罗多那,可难是影取《禅经序》的婆罗陀,而实为舍那婆斯的改写。不如蜜多与般若多罗,就是《禅经序》中的富若密罗、富若罗。从富若罗受法的昙摩多罗,一向就是看作菩提达摩的。所以《宝林传》的后三祖,还是采用《禅经》。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就不免有信手作的感觉。
《宝林传》作者炬,无疑为一位文学的禅者。八世经以来,江东一带,以诗文著名的僧人不少。如为《宝林传》作序的灵彻,就是一位著名的诗僧。《宝林传》继承敦煌本《坛经》七佛以来的法统,而加以改定。《宝林传》有二十八祖传法偈(现存本缺初品,七佛偈大概是有的),有从来没有听见过的更多故事。据说是依支疆梁楼《续法记》,吉迦烟《五明集》等,但这都是说说而已。据近人的研究,《宝林传》作者,属于洪州门下(如《初期禅宗史书之研究》5·1)。自《宝林传》问世,西天二十八祖的传统,渐成为(禅家的)定论。此后,如唐华岳玄伟,于898—900年间作《玄门圣胄集》五卷。南唐静、筠二禅德,于952年作《祖堂集》二于卷。宋道原于1004年,上呈《景德传灯录》三十卷。宋契嵩于1061年,奏上《传法正宗记》及《传法正宗定祖图》共十卷。这都是以《宝林传》的(七佛)二十八祖传法偈及事迹为基础的。《宝林传》不失为伟大的创作!
敦煌本《坛经》,有关七佛到慧能——四十代的相承(相藏本《坛经》,依《宝林传》改正),是荷泽门下所传,与“坛经传宗”有关,所以接着说:“今日已后,递相传受,须有依约,莫失宗旨!”荷泽门下的“坛经传宗”,不只是“教授一卷坛经”,而且是:“须知法处、年月日、姓名,递相过嘱。无坛经禀承者,非南宗弟子也。”“坛经传宗”,实与后代传法的“法卷”意义相同。禅宗的传法典礼,一直流传到现在。传法的仪式是:法师——传法者登高座,法子——受法者礼拜、长跪、合掌。传法者宣读“法卷”,然后将“法卷”交与受法者。“法卷”的内容是:先叙列七佛。次从西天初祖大迦叶,到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就是东土初祖,再叙列到六祖大鉴慧能(列祖的付法偈,有全录的,有略录的)。如传授者属于临济宗,那就从南岳怀让到“临济正宗第一世临济义玄禅师”。这样的二世、三世,一直到当前的传法者——“临济正宗四十×世××××禅师”。付法与某人,并说一付法偈,然后记“××年,岁次××,×月×日”。这就是传授所用的“法卷”内容。敦煌本《坛经》,不但列举了六代的付法偈,七佛到第四十世慧能的传承,还说:“若不得坛经,即无禀受,须知法处,年月日,姓名,递相付嘱。””坛经传宗“的实际意义,岂不是与传法所用的“法卷”一样吗?洪州门下责难荷泽门下的”坛经传宗“,然而从上已来,师资授受的法统次第,还是不能不有的。到后来,还是模仿“坛经传宗”,改为“法卷”而一直流传下来。“坛经传宗”为荷泽门下法门授受的特有制度。“坛经”中有关“坛经传宗”部分,当然是荷泽门下所补充的了。
南方宗旨
在八世纪末,神会门下的“坛经传宗”以前,南阳忠国师已说到《坛经》被添改了,这就是“南文宗旨”。南阳慧忠的事迹,见《宋僧传》卷九“慧忠传”(大正50·762中——763中);《传灯录》卷五(大正51·244上—245上)。《传灯录》卷二八,附有“南阳慧忠国师语”(大正51·437下—439中)。慧忠是越州诸暨(今浙江诸暨县)人。上元二年(761年)正月,神会去世的前一所,应肃宗的礼请入京,到大历十年(775年)才去世。在没有入京以前,开元年间(713—741年)起,住在南阳龙兴寺,这是神会住过的道场。他曾住南阳(今河南南阳县)白崖党子谷四十多年;曾历游名山——“五岭,罗浮,四明,天目,白崖”等地方。《宋僧传》作“武当山慧忠”,湖北武当山是他住过的地方。总之,这是一位年龄极高(可能超过一百岁),游历极广的禅师。慧中的师承,传说不一。1.“慧忠传”说:“少而好学,法受双峰。”双峰是道信(通于弘忍)的道场,所以有人据此而推论为弘忍的弟子。2.《祖常集》、《传灯录》都说是慧能的弟子。3.是行思的弟子,如《泉州千佛新著诸祖师颂》作:“国师慧忠和尚法嗣司和尚。”(大正85·1322中)“司”是青原行思(该书作“行司”)。4.是神会的弟子,如《宋僧传》卷一o“灵坦传”说:“此人(灵坦)是贫道同门,俱神会弟子。敕赐号曰在慧,”(大正50·767中)灵坦曾来见慧忠,如贾餗《扬州代林寺大悲禅师碑铭并序》(《全唐文》卷七三一)说:
灵坦“以为非博通不足以圆证,故阅大藏于庐江浮槎寺。非广闻不足以具足,故参了义于上都忠国师。由是名称高远,天下瞻修企。将弘吾道,因请出关。天了降锡名之诏,以显其德,时大历八年”。
贾餗碑撰于宝历元年(825年),没有“贫道同门”的话。“参了义于上都忠国师”(僧传作“礼观之”),也不像同门相见的模样。白居易作《西京兴善寺传法堂碑铭并序》,以“武当山忠,东京会”为同辈。慧忠在当时(肃宗、代宗时)是很有影响力的禅师:传说灵坦的赐号“大慧”,是慧忠代奏的。径山法钦(768—770年在京)的赐号赐号 “国一”,是很到忠国师赞同的。慧忠的传承不大明白,所以谁也想使他属于自己一系。说慧忠与灵坦同门,“俱神会弟子”,是神会系灵坦门下的传说。说慧忠“法嗣司和尚”,是表原系千佛省僜的传说。说是慧能弟子,当然是曹溪门一了(慧忠曾游五岭、罗浮,可能参礼过慧能)。从传说的慧忠语句而论,慧忠有独立的禅风,出入于东山及牛头,南宗与北宗之间。《宋僧传》说:慧忠“论顿也不留联迹,语渐也返常合道”。在当时(神会)南顿与北渐的对抗中,慧忠与神会不同,是顿渐并举的。他说:“即心是佛”,与东山门下相合;而在答常州(今江苏武进)僧灵觉时,又称“无心可用”,“本来无心”,与牛头宗相同。他立“无情有性”,“无情说法”,与牛头宗相同,而与神会、(百丈)怀海、慧海说不同。听人传说马大师说“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这才“笑曰:犹较些子”。这都可见慧忠的思想,与曹溪有关,而又近于当时牛头宗学的。
《传灯录》卷二八,传慧忠有这么一段问答(大正51·437上—438上):
南阳慧忠国师问禅客:从何方来?对曰:南方来?师曰:南方有何知识?曰:知识颇多。师曰:如何示人?曰:彼方知识直下示学人:即心是佛,佛是觉义。汝今悉具见闻觉知之性,此性善能扬眉瞬目,去来运用,遍于身中。挃头头知,挃脚脚知,故名正遍知。离此之外,更无别佛。此身即有灭,心性无始以来未曾生灭。身生灭者,如龙换骨,蛇脱皮,人出故宅。即身是无常,其性常也。南方所说,大约如此。
师曰:若然者,与彼先尼外道无有差别。彼云:我此身中一有神性,此性能知痛痒。身坏之时神则出去,如舍被烧舍主出去,舍即无常,舍主常矣。审如此者,邪正莫辨,孰为是乎?吾比游方,多见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众,目视云汉,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坛经改换,添糅鄙谭,削除圣意,惑乱后徒,岂成言教?苦哉!吾宗丧矣!若以见闻觉知为佛性者,净名不应云:法离见闻觉知,若行见闻觉知,是刚见闻觉知,非求法也。
《传灯录》椋蚀鸬娜暮艹ぁ4怼澳戏阶谥肌薄澳献凇钡撵停挂昧恕胺ɑ艘澹鹬保灾っ骷啪踔欠鹦浴s忠赌鶚劸贰袄肭奖冢ㄍ呃┪耷橹铮拭鹦浴保胺鹦允浅#氖俏蕹!保运得魃恚ㄐ模┪蕹#鹦裕ㄐ男裕┦浅!d戏届陀炙担骸坝猩浦妒狙耍旱允缎粤耍蕹#ɡ矗┦迸兹础趼┳右槐咦牛樘ㄖ切裕娜欢ィ馔选!闭庵掷肴瓷硇模橹嵌来娴慕馔压郏灿肷硇奈蕹#ǚ稹⑿模┬允浅5募赝耆嗪稀u馐侵夜λ窃鸬模猿啤澳戏阶谥肌钡募亍!鞍阉尘幕唬眙郾商罚鞒ヒ狻保阂乐夜φ拿魑乃担⒎潜鸬模钦狻吧恚ㄐ模┪蕹#允浅!钡哪戏阶谥肌u庵旨兀欠裢獾酪话悖恐夜φ暮窃穑欠袂〉保空馐橇硪晃侍猓夜λ摹短尘罚延猩砦蕹6ǚ穑┬猿5幕埃堑笔钡氖率怠u庵稚砦蕹6猿6猿5募兀踊壑沂贝ǎ罚担澳昵昂螅恢钡较衷冢急4嬖凇短尘防铩6鼗捅久靼椎乇硎玖苏庵旨兀缢?br> 无住者,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今(原误作“念”)念后念,念念相续(原误作“读”),无有断绝。若一念断绝,法身是离色身。(大正48·338下)
莫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断,即死(原误作“无”),别处受生。(大正48·338下)
色身是舍宅,不可言归。向者三身,在自法性,世人尽有,为迷不见,外觅三如来,不见自色身中三身佛。(大正48·339上)
皮肉是色身,是舍宅,不在归依也。(大正48·339中)
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坏。(大正48·341中)
敦煌本《坛经》,明白表示了色身与法身(又从法身说三身)的差别。皮肉的色身,如舍宅一样;死就是法身离去了色身。这与忠国师所呵责的南方宗旨——色身无常性是常,完全一样。《坛经》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对此要义的开示,也表达了色身无常而性常的意见,明藏本所说更为具体,如:(略)
依《坛经》说,“无念”,不是什么都不念。人的本性,就是“念念不住”的(这名为“无住为本”)。可说“念”是人的本性,是人本性——真如所起的作用。所以“无念”不是什么都不念,不念,那就是死了。眼耳鼻舌是不能念的;六根有见闻觉知,实在是自性——真如的用。所以只要“不住”(住就是系缚),只要“于一切境上不染”,那就是“无念”、“解脱自在”。见闻觉知不是六根所有的,是自性(真如,佛性)的用。离见闻觉知,去来屈申以外,哪里有佛可得?这与忠国师所说的“南方宗旨”,大意是相同的,充其量,说得善巧不善巧而已!
色身无常而性是常,忠国师所见的《坛经》,“自称南方宗旨”,在南方禅客来问答时,更为兴盛了!那位禅客是从“南方”来的。色身无常而性常,是“志方禅客”所传。“南方”,不是岭南,就是长江以南。神会宣扬南宗顿教,也说“无性无佛性”,但身心无常而性是常的对立说,在神会的语录中,没有明确的文证。不能因荷泽门下的“坛经传宗”,而说“南方禅客”代表洛阳神会的宗旨。忠国师所说的“南方宗旨”,洪州门下要接近得多。其实,这是东山所传的禅门隐义,是南宗、北宗所共有的,不过南方特别发扬而已。
“坛经传宗”的添改,为洛阳神会门下约为780—800年间。“色身无常而性是常”的添改,应比“坛经传宗”的添改为早。因为敦煌本——“坛经传宗”本,是在“南方宗旨”本上,增补一些传承依约而成的。那末,“南方宗旨”本是谁所添改的呢?敦煌本《坛经》末,有《坛经》传受的记录(大正48·345中)说:
此坛经,法海上座集。上座无常,传同学道漈。道漈无常,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溪山法兴寺,见今传受此法。
这是《坛经》的附记(与后记一样)部分。这一早期的传受记录,与荷泽神会的传承无关,这是应有事实根据的。道漈为法海的同学,所以悟真是慧能的再传,约为慧能去世后,三十年代(743年前后)的实在人物。这一附记,兴圣寺本作:
泊乎法海上座无常,以此经付嘱志道,志道付彼岸,彼岸付悟真,悟真付圆会,递代相传付嘱。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中现也。
兴圣寺本虽有五传,但没有明说是同学或者是门人,所可以知道的,比敦煌本的悟真,又多传付一人,时代应迟一二十年。二本的传授(不完全是师与弟子的传承)次第,虽小有不合,但仍有共同性,那就是从法海而传到悟真。法海与悟真间,敦煌本是法海的同学道漈,兴圣寺本为志道与彼岸,志道也是慧能弟子——十弟子的一人。《坛经》传到悟真(敦煌本),已有了“南方宗旨”。如真像忠国师所说,南方宗旨是为人增入的,那一定是在法海与悟真之间了,或就是志道吧!《传灯录》卷五(大正51·239中)有志道见六祖的问答:
广州志道禅师者,南海人也。初参六祖,曰:学人自出家,览涅槃经仅十余载,未明大意,愿和尚垂诲!
祖曰:汝何处未了!对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于此疑惑。
祖曰:汝作么生疑?对曰:一切众生,皆有二身,谓色身、法身也。色身无常,有生有灭。法身有常,无知无觉……
志道是广州南海人,他的“色身无常,法身是常”的对立说,与慧忠所知的“南方宗旨”,《坛经》中“色身无常而性是常”的见解相近。《坛经》的色身无常,法身是常说,如作为志道传的添改本,应该是非常合适的。慧能是岭南人,在岭南曹溪开法。慧能的弟子,或早已离去。或去世后离去。过长江而北还河洛传禅的,是神会、慧忠、本净、自在等。在长江以南——湖南、江西弘传的,是怀让、行思等。以曹溪为中心的岭南,禅风并没有息迹。在传说中,有法海、志道他们。南方宗经,推定为六祖的晚年(或再传)弟子,从曹溪流传出来。
坛经的初期流变
敦煌本《坛经》,为现存各本中最古的,然至少已经过“南方宗旨”、“坛经传宗”的改补。“坛经传宗”为780—800年间。早在750年顷,慧忠见到了“南方宗旨”的添改本。据此可见慧忠早年,会见过《坛经》原本,否则怎么知道有了添改呢!《坛经》从成立而到敦煌本阶段,再叙述如一:
一、《坛经》有原始部分,附编部分。《坛经》从大梵寺开法——“法坛”或“施法坛”的开法记录得名,是主体部分。大梵寺开法,到底在什么年代,没有明文可考,大抵为慧能晚年。这一部分的成立,是慧能生前。附编部分,是慧能入灭以后,将慧能平日接引弟子的机缘、付嘱、临终的情形、身后安葬会等,集录而附编于《坛经》,也就称为《坛经》了。敦煌本所说,付嘱十弟了,及记录少数弟子的问答,那只是集录者,就慧能晚年随侍的弟了,记录一二,并非全部(应更有慧能的事迹,问答机缘,传说在众弟子间)。这决非如或者所说,荷泽门下故意将南岳、青原的机缘删去了。
《坛经》是弟子法海所记(附编部分,应说是“所集”),是《坛经》自身所表明的。敦煌本末了说:“和尚本是韶州曲江县人”,指集出而传授《坛经》的法海,就是《传灯录》“韶州法海禅师者,曲江人也”的根据。《历代法宝记》说:“曹溪僧玄楷、智海等问和上:已后谁人得法承后。”(大正51·182下)智海,应就是《坛经》的法海。法与智,传说不一,如《宝林传》作者法炬,也有传为智炬的。
《坛经》延祐(1316年)本,在德异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序》后,有“法海集”的《略序》。这篇
《略序》,(1291年)宗宝本属于《坛经》的附录,题为《六祖大师缘起外纪》。明藏本(1440年)相同,作“门人法海等集”。《略序》,编入《全唐文》卷九一五,都是看作法海所作的(“略序”所说,与《坛经》每每不合,决非《坛经》记录者法海所作。这是与《瘗发塔记》、《别传》为同一系的作品。)《全唐文》在《略序》前,编者附记说:
法海,字文允,俗姓张氏,丹阳人。一云:曲江人。出家鹤林寺,为六祖弟子。天宝中,预扬州法慎律师讲席。
鹤林寺法海,《宋僧传》(卷六)有“吴兴法海”传。鹤林法海为鹤林玄素(668—752年)弟了。李华撰《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说到“门人法励、法海”(《全唐文》卷三二o)。鹤林法海与昙一(692—771年)、灵一(728—762年),参与扬州龙兴寺法慎律师(748年去世)的讲席。与杼山皎然为“忘形之交”。颜真卿撰《湖州乌程县杼山妙喜寺碑铭》,说到大历所间,集《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金陵法海”与皎然,都是主持编务的(《全唐文》卷三三九)。鹤林法海约卒于780年顷,在慧能灭后六十多年,不可能是曹溪慧能的弟子。曲江人法海,并非丹阳法海。只是《全唐文》编者,想从高僧传里,求得慧能弟子法海的事迹,见到了吴兴的鹤林“法海传”,以为就是集记《坛经》的法海,也就臆说为:“出家鹤林寺,为六祖弟子。”《全唐文》编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离慧能入灭一千一百多年了,凭什么说鹤林法海是六祖弟子呢!这是毫无根据的!中国佛教的史传,详于江、河一带(中原),对于边区,一向都资料不足。曹溪门下而在岭南弘法的——法海、志道、悟真他们,都传记不备。然而不能为了求证,而乱指为鹤林法海,或否定法海他们。在“坛经传宗”以前,慧忠所见“南方宗旨”本是添糅以前,《坛经》原本早已存在,为慧能门下所知。是谁所记(集)的呢?总不能没有人,那就是《坛经》所说的曲江法海。
二、法海所记所集的《坛经》原本,流传于曹溪,可称之为“曹溪砂本”。敦煌本说到:“此坛经,……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曹溪山法兴寺,见今传受此法。”可见敦煌本所依的底本,是从悟真所传来的。悟真为慧能的再传弟子,弘法的时代,约为750年前后。兴圣寺本小有出入,叙述到悟真传弟子圆会,那是同一本而多传了一代。悟真以前有志道,思想与“南方宗旨”相近,所以推定为:悟真所传,敦煌本所依的底本,是修改过后“南方宗旨”本。由于南方宗旨的增润,引起忠国师的慨叹——“添糅鄙谭,削除圣意”。
三、神会门下为了维护神会以来的正统说,所以补充悟真所传的南方宗旨本,成为现存的敦煌本。《坛经》在曹溪,是手抄秘本,在少数人中流传,被重视而尊为《坛经》。这部手写秘本,在曹溪早就有了次第传授的事实。如法海付道漈,道漈付悟真。禅者是不重文记的,所以虽知道的这部《坛经》,也没有过分的重视。等到悟真本传入京洛,神会门下利用这次第传授,而加旨其意义。以“禀承坛经”,为“南宗弟子”的依约,补充付法统系而成为“坛经传宗”本。这一偏重文字、偏重形式的传授,受到洪州门下的评击,然《坛经》也就从此大大地传开了。
敦煌本《坛经》,是经一再地修改添糅而成的。“南方宗旨”与“坛经传宗”的特色,可以明确地看出,但由于杂糅为一,实已无法明确地逐段分离出来,回复曹溪原本的初形。宇井伯寿作《坛经考》,在铃木大拙区分全部为五十七节的基础上,保留了三十七节为原本,以其余的为神门下所增前益。但他的方法是主观的,不容易为人所接受。就现存的敦煌本来就,曹溪原本归南方宗旨所杂易为人所接受。就现存的敦煌本来说,曹溪原本归南方宗旨所杂糅,不易逐段地分别,然对神会来说,这是与神会无关的。敦煌本特别重视“自性”,“自性变化一切”,这是神会禅学所没有的。法身与色身的对立,色身离法身就是死了的见地,在有关神会的作品中,也没有发现。神会专提“不作意”,而敦煌本却一再说到“作意”。总之,神会决非以经过南方宗旨添糅过的《坛经》为依据的,神会也不会造这南方宗旨所杂糅了的《坛经》。“坛经传宗”,是在南方宗旨杂糅了的《坛经》上,增入有关法统传承,及赞誉神会部分。至于其他所说,《坛经》与神会所传近似的,那只是神会所禀承的,与《坛经》所依据的,同源于曹溪慧能而已。
《坛经》的一再增改,或是一段一段的,或是插几句进去。好在禅师们是不重文字的,虽一再地添糅补充,却没有注意到文字的统一性,所以有文意重复,文义不衔接,文笔前后不一致的现象。试略举二例:一、从文字的称呼上看出先后形迹:如大梵寺说法部分,对于慧能,集记者称之为“慧能大师”、“能大师”、“大师”。慧能自称为“慧能”、“能”。大众称慧能为“和尚”。慧能称大众为“善知识”,称刺史为“使君”。这种称呼,是吻合当时实情的。偶有二处例外——“六祖言”,杂在“释疑”中间,那就是后来增补的部分。“附录”的弟子机缘部分,对于慧能,编集者也称之为“大师”、“能大师”、“慧能大师”。学人称慧能为“和尚”。慧能自称为“吾”,称学人为“汝”、“汝等”,或直呼名字。除三处例外——“六祖言”,与当时的实际称呼不合(与志诚问答中,编集者偶称慧能为“慧能和尚”,也疑为杂入的)。临终部分,也合于上述的体例。而告别部分,主要是“坛经传宗”。编集者称慧能为“六祖”,弟子称慧能为“大师”,都与当时的实际称呼不合。又如编集者说“上座法海向前言”,更可看出后人增附的了。发现了称呼上的差别,对于某些是增补的,多一层客观的标准。
二、从文字的不统一看出先后的不同:梁武帝与达摩问答部分,敦煌本一律作“达磨”;而有关法统传承部分,却写作“达摩”。如出于人手笔,前后不应如此的差别。考神会门下所记的《南宗定是非论》,是写作“达摩多罗”与“菩提达摩”。写作“达摩”,与神会门下(“坛经传宗”)增补的法统传承相合。第一章曾说到,称为“菩提达磨”与“达磨多罗”,是传说于南方的,所以达磨与梁武帝的问答,应该是南方宗旨杂糅本。还有,自称为“我”或“吾”,在敦煌本中是大有区别的。“附录”部分,是一概自称为“吾”的。而大梵寺说法——“坛经主体”,大体是自称为“我”的,不过也偶尔有几个“吾”字(这可能是为杂糅所乱)。从这两部分自称为“我”或“吾”不的同,也可见集出的不同一人了。从文字去分别先后,这只是聊举一例,用备研究者的参考。
第三节 坛经的变化
从《坛经》原本到敦煌本,至少已有过二次重大的修补。此后,流传中的《坛经》,不断的改编,不断的刊行,变化是非常多的。宇井伯寿所作《坛经考》,论究得相当完备。今直依《坛经》本文,不论序、跋、历朝崇奉,略说大概。
组织与内容的变化
《坛经》的各种本子,从大类上去分别,可统摄为四种本子:敦煌本、古本、惠昕本、至元本。
“敦煌本”:为近代从敦煌所发现的写本,为神会门下“坛经传宗”的修正本,约成立于780—800年是。其内容,大体为以后各本所继承。敦煌本所说的无相戒,形神对立,慧能事迹,传承说,都与神会的传述不合。所以,敦煌本所依的底本,不是神会一派所作,只是神会门下依据悟真所传的本子,多少补育而作为“传宗”的依约而已。
“惠昕本”:铃木大拙出版的兴圣寺本《六祖坛经》,有惠昕的序文说:
我六祖大师,广为学徒,直说见性法门,总令自悟成佛。目为坛经,流传后学。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余以太岁丁卯,月在蕤宾,二十三日辛亥,于思迎塔院,分为二卷,凡十一门,贵接后来同见佛性者。
惠昕本,分二卷十一门。编定的时间,考定为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年)五月。惠昕本于政和六的(1116年)再刊,传入日本,被称为“大乘寺本”。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刊本,传入日本,被称为“兴圣寺本”。大乘寺本与兴圣寺本,品目与本文,虽有多少修改,但分为二卷十一门,是相同的,都是惠昕的编本。兴圣寺本序下一行题:“依真小师邕州罗秀山惠进禅院沙门惠昕述”。“依真小师”的意义不明,“小师”或是“门师”的讹写。“邕州”,即今广西省的南宁县。“惠进禅院”,即序文中的“思迎塔院”,思迎应为惠进的讹写。“惠昕述”,其实是改编。由于“述”字,有人就误解为惠昕所作了。如1151年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就说《六祖坛经》三卷(或作二卷)十六门(应是十一门),惠昕撰。惠昕本,对敦煌本来说,有所增订。如增入“唐朝征召”部分;传五分法身香;慧能得法回来避难等事迹。次第改定的,是有关授无相戒的次第,如:(略)
关于“弟子机缘”,惠昕本还只是志诚等四人,与敦煌本相同。“坛经传授”,从法海一直传到圆会,主要是多传了圆会一代。而敦煌本中,从二祖到五祖的付法偈,六祖所说的二颂,及末后“如付此法”等附记,惠昕本缺。这可以推见“惠昕本所依的底本,近于敦煌本,是圆会所传本。在这人基础上,参考古本而改编成的。
“至元本”: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德异在吴中刊行《坛经》,序文说:
坛经为后人节略太多,不见六祖大全之旨。德异幼年,尝见古本。自后遍求三十余载,近得能上人寻到古本,遂刊于吴中休休禅庵。……至元二十七年庚寅岁中春月叙。
德异本,在日本元延祐三年(1316年)刻本,称为“元祐本”,是经高丽而传入的。德异本翻刻本极多,憨山大师重刻的曹溪原本,也就是这种本子。依德异的序文,所见的“坛经为后人节略太多”,可能指惠昕本而说。又说从通上人得到的古本,就是三十多的前见过的,就把古本刊出来。到底是刊行古本,还是有所增减呢?德异的至元本,与惠昕本相比,显然是文名增广了。凡惠昕本所有的,如“传五分法身香”、“唐朝征召”等,至元本也是有的。内容上,“弟子机缘”是大大增广了,大致与《景德传灯录》相近。组织上,将说般若波罗蜜法,与功德及净土的问答,提前而编于“得法传衣”之后。
与德异本相近的,有宗宝本,宗宝的跋文说:
余初入道,有感至斯。续见(《坛经》)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灭。因取其本校雠,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机缘,庶几学者得尽曹溪之旨。……至元辛卯夏,南海释宗宝跋。
宗宝自署为“南海释宗宝”,传说为“风幡报恩光孝寺”的住持。依跋说,刊行于至元辛卯夏,即1291年。依三本而校为一本,又加入“弟子机缘”。明太祖(1368—1398年),成祖(1403—1424年)刊行大藏经(南藏、北藏),将宗宝本编入大藏。大正藏经的《六祖大师法宝支经》,也是依北藏而编入的。从内容看来,宗宝本与德异本,组织上最为一致。对宗宝的后跋,至少有三点可疑:1.德异本刊于吴中,时间是1290年春。宗宝本刊于南海,时间是1291年夏。同一组织系统的本子,在距离那么远的地区,竟同时而先后地刊出,不太巧合吗?宗宝本能没有依据德异本吗?2.即使说,宗宝依据的三本,有一本就是德异所得的古本。那末,“弟子机缘”早已有了,宗宝怎么说自己加入呢!3.德异刊本,前有德异序。而宗宝本,将德异序刻在前面,宗宝的跋文刻在后面,这至少表示了——宗宝本是依据德异本,再加精治:“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宗宝本的刊行,应该迟多少年。跋文说“复加入弟子机缘”,“至元辛卯夏”,只是为了隐蔽依据德异本的事实,故弄玄虚!
“古本”:在古人记述中,知道《坛经》有古本(或称“曹溪古本”)存在。如惠昕本惠昕序说:
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先忻后厌。
惠昕作序于967年。惠昕因为古本文繁,才删略为二卷本的。惠昕所见的古本,文段繁长,至少是九世纪本。宋契嵩也曾校定《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至和二年(1056年),吏部侍郎郎简作序说:
六祖之说,余素敬薄;计湮自鏊穑淖直少捣痹哟豢煽肌;嵘趁牌踽蕴尘蓿蛭结允υ唬喝裟苷蔽霾颇s。怨闫浯8兀怨貌芟疟荆v粘扇恚尤唤粤嬷裕桓疵d嗣わ伟澹约涫な隆v梁驮耆率湃招颉?br> 郎简所见的《坛经》,“文字鄙俚繁杂”。“繁杂”,与九十年前,惠昕所见的“古本文繁”相同。契嵩得到了“曹溪古本”,校为三卷,大抵是依据古本,而作一番文字的修正、润饰。从三卷来说,篇幅不少。契嵩曾作《坛经赞》,所叙述的大梵寺说法部分,与敦煌本次第相合,也没有“五分法身香”。所以契嵩的三卷本,可能大梵寺说法部分,与敦煌本相同。而在其他部分,大大的增多,与古本要近。到契嵩时,应有繁杂鄙俚的古本,契嵩勒成三卷的曹溪古本。
比对惠昕本,至元本,与敦煌本的不同,除次第变动,及增“五分法身香”外,主要为二大类:慧能的事迹,弟子的机缘。说到慧能的事迹,敦煌本最为古朴。但在八世纪中,更有不同的传说。如《神会语录》(石井光雄本),《历代法宝记》(及《圆觉经大疏钞》),是荷泽门下所传的,对《坛经》的影响不大。如法才的《光孝寺瘗发塔记》、《别叙》(即《六祖缘起外纪》)、《曹溪大师别传》:这一系的传说,出渊源于曹溪,成为荷泽门下的别派。所传的慧能事迹更多,与《坛经》大有出入。《别传》的成立,对后来禅宗(洪门、石头门下)的影响很大。《宝林传》修正了《别传》的二十八祖说。《宝林传》的六祖传,虽佚失而没有发现。然从《祖堂集》、《传灯录》、《传法正宗记》等,初祖、二祖、三祖的事迹,都与《宝林传》相合,可推断《传灯录》等所传六祖事迹,都是继承《宝林传》的,都是采录《别传》的传说,而多少修改。如慧能去曹溪,见无尽藏尼等;得法回南方避难,见印宗而出家等;受唐室帝后的礼请,请问、供养等。这些都出于《别传》,为惠昕本、至元本(或多或少)所采录。传说:惠昕嫌繁,节略了古本;德异嫌简,又采取之古本(二本都有次第的改编,文字的修正)。“文繁”与“繁杂”的古本,一定是将《别传》的传说,编入》坛经》而成。同时,慧能与弟子的问答机缘,传说在当时的,也采录进去,成为“繁杂”的古本。虽不知编者是谁,但属于洪州门下,与《宝林传》异曲同工,是没有疑问的。这虽被称为古本,而成立的时代,要比敦煌本(780—800年)、《别传》(781年)、《宝林传》(801年)迟些。
名称的变化
一般来说,《坛经》是最根本的、公认的名称。如《坛经》本文,南阳慧忠、韦处厚、惠昕、《传灯录》、《传法正宗记》都是直称为《坛经》的。现存的敦煌本,题目很长,包含有几个名字(这是模仿经典的),是:
南宗顿都最上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
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这一题目,应加以分析。《坛经》开端说:“慧能大师于大梵寺讲堂中,升高座,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受无相戒。……令门人法海集记。”依经文,“慧能大师于梵寺……说”,是说者与说处。“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受无相戒”,是所说的法门内容。“门人法海集记”,是记录者。据此来考察题目:“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这里面,“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是说者与说处。“施法坛经”,是一部的主名。“人法双举”,是经典的常例。“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兼受无相戒”,是标举法门的内容。敦煌本写作“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大正藏》才排成“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以“兼受无相戒”为法海的学历,显然是误解了。还有“南宗顿教最上大乘”,与经末的“南宗顿都最上乘坛经法”相合。这一名称,一般解说为荷泽门下所附加,大致是正确的。“六祖慧能大师于大梵寺施法坛经”,为一部的正名。“施法坛经”,或简写这“法坛经”(倒写为“坛经法”)、《坛经》,都说明了是大梵寺的开法传禅。
惠昕的节略本:惠昕序,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兴圣寺本,作“六祖坛经”。大乘寺本作“韶州曹溪山六祖大师坛经”。这可说是从(敦煌本)“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的简化而来。日僧圆珍来唐取回经像,(858年)所作的目录,如《智证大师请来目录》,有“曹溪能大师檀经一卷”(大正55·1106下)。《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经律论疏记外书待目录》,有“曹溪山第六祖能大师坛经一卷”(大正55·1095上)。这一名称,都是与敦煌本、惠昕本的取意相近的。
“古本”与“至元本”:郎简作《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记序》说:“法宝记,盖六祖之说其法也。”“法宝记”,“法宝坛经记”——以“法宝”为《坛经》的题目,是契嵩所改古本。后来自称重刊古本的德异本,作“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序”;经末题为“六祖禅师法宝坛经”。宗宝本也名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从古本而来的至元本,题目有“法宝”二字,这是依古本“法宝记”而来的。“法宝记——这一名目,也见不日僧的经录。圆仁(844—848年)来唐取经所作的《入唐新求圣教目录》,有“曹溪山第六祖慧能大师说见性顿教直了无疑决定成佛法宝记坛经一卷”(大正55·1083中)。据此推论,改“法坛经”,“施法坛经”为“法宝坛经记”,844年前已经存在了。古本用此名称,可推见在《别传》、《宝林传》成立后,就已开始更多采录而成繁长的古本了。说到“法宝记”,在禅书中是有悠久渊源的。开元中(713年—?),神秀门下杜胐,作《传法宝记》。大历中(775年—?),保唐门下作《历代法宝记》。这都是代代相承的灯史;所以“法宝”是人宝,师资相承,利益众生。《历代法宝记》中,诸祖及无住为弟子开示很多,有法宝的意义。建中中(781年),洪州门下慧炬,作《宝林传》。宝林不只是曹溪的宝林寺,也是西天东土历祖相承的宝林。洪州门下编集的古本《坛经》,据朗简序,是名为“法宝记”或“法宝坛经记”的。“宝”为洪州门下所采用;“法宝记”,“宝林传”,都从古代的《传法宝纪》、《历代法宝记》的“法宝”演化而来。
编辑:几根竹条
上一篇: 不空三藏法师(西元705~774年)
下一篇: 玄奘——佛经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