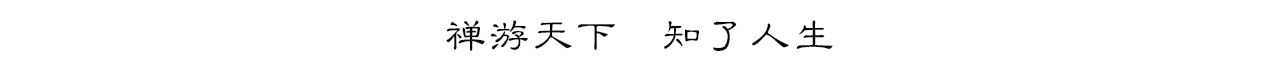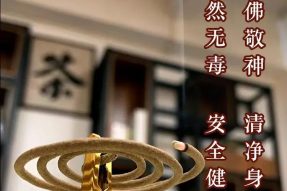从谂法师(西元778~897年)
赵州从谂和尚,山东人,俗姓郝。十八岁参於南泉,有所契悟;嵩山受戒以後,返回南泉。六十岁以後,历访黄檗、宝树、盐官、夹山等。请住河北赵州观音院,大振南宗於北方,传为赵州禅,闻者无不信服。圆寂时一百二十岁, 「真际大师」。
赵州住院四十年,活用三祖言句,使用口唇棒喝,公案很多,禅客亦属不少。
赵州初参南泉,恰巧南泉卧在安乐椅上休息,看见赵州来,就问∶『你从那里来的?』州∶『从瑞像来。』泉∶『见过瑞像吗?』州∶『不见瑞像,只见卧如来。』南泉著急,站起来说∶『你是有主(师)的沙弥麽?』州∶『我是有主的。』泉∶『那一位是你师?』赵州合掌礼拜云∶『仲冬严寒,伏惟和尚尊候万福。』以後准他入室。
赵州问∶『道是什麽?』泉∶『平常心是道。』州∶『那麽,是不是不必修行?』泉∶『如果你要找些线索,道就没有了。』州∶『可是不捉些什麽时,还有道麽?』泉∶『所谓道,不在知不知(对立)。若说有了见道的,那个知,就是妄觉;又不是不知,却是无记。到了不疑时,太虚廓然,事物融合,不要在分别上,批判是非。』
赵州与投子大同(?~八一四年)是同时代的大宗师。赵州属於南岳系统,投子是青原系统。投子大同∶安徽怀宁人,姓刘。遁居安徽桐城投於山三十馀年。赵州行脚六十年,一日来到桐城,恰巧投子下山,路途相逢。州∶『是不是投子山主?』大同∶『茶盐钱来布施吧!』只此一问一答,就分别了。赵州到庵,坐下,庵主带一瓶油回来。州∶『久仰投子高名,到来一看,不过是个卖油翁,那一个是投子?』投子提起油瓶∶『油呀!油呀!买油麽?』(是非交接处,圣也不能知,是是非非是分别智。)州∶『大死的人,却活,是如何?』(死人还生,是鬼怪;大死的人,却有再活的。死到大死,则大活现前。)大同∶『不许夜行,投明须到。』(明天走吧!圆转的宗旨。)
赵州云∶『如明珠在掌,胡来胡现,汉来汉现,老僧把一枝草为丈六金身,把丈六金身为一茎草;佛是烦恼,烦恼是佛。』
僧问∶『如何是平常心?』州∶『狐狼野干就是。』问∶『道是什麽?』州∶『墙外就是。』僧∶『我问的不是那个道。』州∶『你问的是那一条道?』僧∶『是天地的大道。』州∶『呵!大道透过长安首都。』僧∶『至道无难,唯嫌拣择,稍有语言,即是拣择,和尚怎样为人举示?』州∶『何不引尽这语?』(尚有下句)僧∶『某甲只念到这里。』州∶『只这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不要妄想)(碧岩录)
僧∶『初生孩子,还具六识也无?』如果有,怎麽不能分别?否则,怎会啼哭?州∶『急水上打球子。』间不容发。僧问投子∶『急水上打球子,意旨如何?』投於∶『念念不停流。』
僧∶『什麽叫作思忆不及?』州∶『你过路来吧!』僧∶『过路来,还是思忆可及。』赵州举手云∶『这个,你说,是什麽?』僧∶『手呀!和尚怎麽说?』州∶『要我说,我可说得许多名称。』僧∶『我不问许多的名称,要问和尚怎样说?』州∶『是麽?那就是你思忆不及的地方啦!』僧下拜,州∶『我来告诉你,思忆可及的地方好麽?』僧∶『是什麽啊?』州∶『释迦佛的教法,祖师的教法,都是你的老师呢!』僧∶『佛祖,祖师们的教法,古人都说过了。』赵子又举手问∶『你说,这是什麽?』僧默然,州∶『怎麽不当面速答?那里有可疑的地方?』疑即涉及分别。出手就手,出指就指,一念不生,万事成就。
僧∶『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如何是不拣择?』照道实行容易,出了分别就不容易了;该僧以为拣择怎麽不好?州∶『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没有对立,没有拣择,才是无难的至道。僧∶『唯我独尊,还是拣择。』不是你我的我,又不是尊卑的尊。州∶『田舍奴,那里是拣择?』僧无语。(碧岩录)
赵州有石桥,僧来试探∶『久闻赵州石桥,到来一看,不过是个独木桥呢!』赵州佛法,并不高贵。州∶『你只看了独木桥,还没有看到石桥呢!』僧∶『什麽是赵州石桥啊?』(分别了)州∶『渡驴渡马。』万法即真如。
僧∶『至道无难,唯嫌拣择,是时人的毛病麽?』指摘赵州。州∶『曾有人问我,直到五年,分疏不下。』对不住,不但是我,不止五年;十方三世佛,都不说一字,何必再问?(碧岩录)
僧∶『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州∶『我曾在山东青州,订制了一套棉衣,七斤重。』道不远求,无须多说。
僧∶『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州∶『庭前柏树子。』僧∶『和尚,莫将境示人。川∶『老僧未曾将境示人。』僧∶『如何是西来意?』州∶『庭前柏树子。』(无分别智)
僧∶『听说和尚曾参於南泉,是不是?』知而故问,是也三十棒,不是也三十棒。州∶『镇州出大萝卜头。』向南拜北斗,否则迫死赵州。僧∶『什麽叫做赵州?』人、城、地,是问那一个?州∶『东门、西门、南门、北门。』赵州通大道,坏人通不过。
某日镇州大王到赵州,侍者报告∶『大王来了!』州∶『大王万福!』侍者∶『大王还没到山门呢!』州∶『大王来也!』
有婆子在台山路傍开茶店,行脚僧用茶後,问∶『那一条是上台山的路啊?』婆子∶『一直去吧!』该僧跑了二三步,婆子自云∶『这个阿师,又是一样的走了。』不止一次二次。赵州打听了∶『那麽,我本身前往,试试看!』州∶『婆婆啊!跑上台山的路,是那一条啊?』婆∶『一直跑上去就好哪!』赵州跑了几步,婆子∶『好个阿师,又恁麽去也!』赵州不说什麽,回山示众云∶『那个婆於,今天给我彻底的看破了!』(看破∶一念不生的自觉)。
赵州示众云∶『此间的佛法,说是深,却是浅;说是浅,却是深。别处的,见难识易;我这里的,易见难识,会得这个,可能横行天下。或问你从那里来?若说从赵州来,那是诽谤赵州的;若说不从赵州来,又不真实,怎样答得好呢?』僧问∶『无论那一边,都是诽谤和尚。怎样才是不诽谤?』州∶『你说不诽谤,老早诽谤了。』僧∶『学人想学,又是诽谤和尚,究竟怎样才好呢?』州∶『你名叫什麽?』僧∶『我名叫道皎。』州∶『快走吧!饭桶!』这里有了好几个对立∶难易、见识、别处这里、来不来、谤不谤。
严阳间赵州∶『一物不将来时如何?』州∶『放下著。』严∶『一物不将来,放下个什麽?』州∶『恁麽,担取去。』(从容录)
杭州多福,嗣赵州,因僧问∶『如何是多福一丛竹?』福∶『一茎两茎斜,三茎四茎曲。
(曾普信著)
上一篇: 道楷法师(公元1043~1118年)
下一篇: 晁说之居士(西元1059~112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