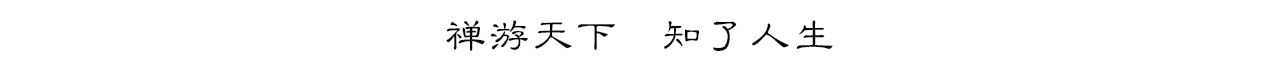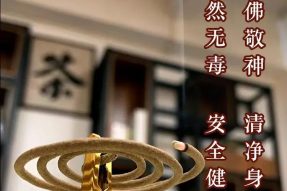印度朝圣:恒河之畔的生死轮回

 在德里街头,每逢周末总能看到乞丐们成群结队接受布施的场景。行乞在印度并不是一种见不得人的生存方式,乞丐们的生活甚至称得上怡然自得。
在德里街头,每逢周末总能看到乞丐们成群结队接受布施的场景。行乞在印度并不是一种见不得人的生存方式,乞丐们的生活甚至称得上怡然自得。 大菩提塔的外貌不似佛教建筑,反而较为接近印度教塔寺,其原因可能是,在12 ~ 14世纪、它最后三次重修期间,印度教元素的大量渗入。
大菩提塔的外貌不似佛教建筑,反而较为接近印度教塔寺,其原因可能是,在12 ~ 14世纪、它最后三次重修期间,印度教元素的大量渗入。 同一条恒河,在外国人眼中,可能仅仅是一桩印度奇景,是肮脏和混乱的最典型示范;但在印度人眼中,她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神圣和包容,人们不远万里来此沐浴,以洗去身上的罪孽。
同一条恒河,在外国人眼中,可能仅仅是一桩印度奇景,是肮脏和混乱的最典型示范;但在印度人眼中,她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神圣和包容,人们不远万里来此沐浴,以洗去身上的罪孽。撰文:梁文道
摄影:王寅
想象你在北京包了一辆车,打算去山西大同参观石窟。一宿之后,你发现自己居然醒在沈阳。而那位司机,他坚持自己的路线正确,并且保证目标在望。再过半天,我们发现自己几乎快要去到哈尔滨了。这时司机才勉强停车问路,但他问路的方式是随便截住一个路过的村民,看他晓不晓得云冈石窟怎么走。真妙,那个村民竟就认真地指起路来:“前面十字路口左转,再过三里地看见公交站右转直行……”
我没有夸张,这个假想的例子只是为了方便读者了解我们一团人刚到印度头两天的真实情况。回来好几个月了,我仍然清楚记得那个旅行车司机,固执而沉默。每回休息他就一个人走开,独自低头喝茶或者吃饼,偶而抽一根烟。每回开车他都全神贯注,遇到任何一个标识不明的分岔路口都果决转向;尽管每一次转向后来都被证明是错的。由于他的方言口音比较重,车上就算有两位印度本地的法师,也要经过三轮传译,才能有效沟通。那种沟通其实也说不上是什么沟通,因为他大部分时候都只会简单地回答一两个字,意思是“OK”和“没有问题”。就在这迷途的两天,就在这位司机身上,我学到了印度教给我的第一课:但凡有人和你说“OK”或者“No Problem”, 那就表示问题一定要发生,而且可能很严重。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是应该更小心,戒惧,提防任何事任何人?还是干脆认输,听天由命呢?答案要到此行的最后,我才有点模糊的轮廓。
这不是一般的旅行观光,我们是朝圣者。去印度朝圣?这对许多中国人来讲都是一个很陌生的事,虽说中国可能拥有全球人数最多的佛教徒,但大家对于回到佛教诞生地这事好像都不太感兴趣。如果真要朝圣,为什么不去五台山、普陀山,甚至少林寺呢?就连教科书都会告诉你,佛教源起印度,但也在印度衰落;而中国却把它发扬光大,传布四海。没错,佛教确实大盛于汉地,所以也兴旺到了可以自成一国的地步,旺到了几乎可以忘掉佛教世界其他地方乃至于印度的程度。在那十几天的旅程里头,我们碰过一家藏人,分别从拉萨和加德满都出发,会合于现处尼泊尔境内的佛陀诞生地蓝毗尼,这一家人打算周游圣地90天。我们也碰到了络绎不绝的泰国朝圣团,一来就是几辆大巴,每到一处就留下遗迹上如鳞密布的金箔。从佛陀初转法轮的鹿野苑,到佛陀入灭的拘尸那罗,藏传佛教徒系在树上的风马旗与南传佛教徒贴在石柱上的金箔都是至为显眼的标识。我甚至看见日本日莲宗四处立下的《南无妙法莲华经》石碑,以及无数操着多国语言的金发香客,唯独极少遇见汉地来的朝圣者。如果有的话,那也多半是台湾佛教徒。如今大陆出国的人绝不算少,为什么我们在全球各大传承各大宗派汇聚的这片北印度土地上却很难看到他们呢?
不过话说回来,所谓“朝圣”,对佛教徒而言或许根本就是一个很可疑的概念。我们知道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去罗马、去耶路撒冷,即便不是指定作业,至少也是种普遍被推崇的行动。中古时代,“到圣地去”甚至是发动起整场十字军东征的最大口号。至于穆斯林,那就更不用说了,朝觐麦加乃毕生必行的“五功”之一,没有能力走上一趟往往是他们抱憾终身的遗恨。但佛教徒呢?日本有它的高野山,西藏有纳木错湖与冈仁波齐峰,汉人则有九华峨嵋,大家尽管在境内各自修行,从来没听过非得回到菩提迦耶目睹佛陀证道地不可这一说。
所以印度佛教衰亡之后,佛陀一生行止的遗迹也就彻底败坏了,或者成为砖瓦供后来的穆斯林苏丹建造华贵如天堂的城堡,或者埋没沙土年复一年直至荒草遍野。千年中并没有大群比丘如伯利恒的神父那样坚守据点以维持香灯不坠,更没有哪一个帝王忽然跳出来号召大家“去把圣地从异教徒的手中夺回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圣地其实大多是由碎石与传说编撰而成。比如说祇园精舍,佛陀驻锡最久之地,考古学家挖出一片房舍的地基,认为它们全是公元后5、6世纪左右的遗物。热心的信徒们偏能认出哪一间是公元前5世纪时舍利弗尊者的居室,哪一处又是圣弟子们经行的步道。就算是那些看起来颇有年岁的遗址,你也不能不怀疑它们的真确,因为那天我分明看到一群工人搬砖垒石,好像正在建筑另一间“遗址”的样子。
上一篇: 印度朝圣:佛陀说法台灵鹫山